19
2023年,一如往常地紛亂。
加薩走廊烽火連天、尼日政變局勢動盪、緬北軍民衝突持續升級。當彈藥炮響在世界各地此起彼落,全球通膨與供應鏈面臨重組壓力,此時福島核廢水已被排放入海。
世界各地的戰爭、災禍與苦難從未停歇,而台灣內部的#MeToo潮、社子島開發、竹科龍潭園區擴張、職安法改革怠慢、近八萬五千名移工失聯……,大小層級不一的區域性議題,都讓我們對這些抗爭的切身性與否,作出了自己的立場判準。作為藝術工作者,我們在超載、過剩的國內外事件與現實議題下,選擇在不同尺度上衡量自身與現實世界的緊密度與相關性。事實上我們所能夠付諸心力的,也永遠不比我們的表態與立場來得更為前瞻。
藝術的使命感:我們對現實的愛恨
「藝術不是反映現實的鏡子,而是鑿作現實的鐵鎚。」這句述及藝術與現實的至理名言,來源已不可考;有說法是馬克思所言,也有的說是布萊希特,或是托洛茨基(Lev Davidovich),也可能是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或許,是誰說的一點也不重要,因為當這句曠世標語在今天被印製於世界各地的大小海報、明信片、馬克杯上,彷彿曾經徵引過這句話的上述人物及其社會主義信奉者的身分,也終將隨著時代的失憶而失去了溯源的必要性。
過去20年,台灣當代藝術、表演藝術的生產鏈上大幅崛起的藝術田野、人類學與民族誌轉向、社會參與藝術的興起——藝術為政治的不自由發聲、為歷史的不鬆動改寫、為社會的不公義請命——從一開始亟欲逸脫自帝國主義視角的台灣史、西方知識殖民本位的台灣藝術論述,然而到了今天,這一切看似鑿作現實的鐵鎚都已然尋常得令人感到麻木不仁。當文化政治變成當代文化必須政治,縱使我們並非要去批判計畫型創作過度擁抱社會學方法導向,也必然深諳要被重視就得學習該如何拿出可被立即辨識的個人性格與觀照世界的態度與本領。也恰因如此,社交媒體成為我們最快識別同袍與暗敵的名片,我們對藝術家或藝術作品的態度,很快即被群體中的多數歸納到給定的戰場之中。
對於每個人心中該如何親近外部世界並與之產生關係,我們人人心中有數。不過,畢竟還是藝術工作者的我們,多少也都還是對現實世界抱持著最基本的人文關愛與人道關懷——於是,我們總是盡可能不過不失地藉由創作、策展、評論來表達我們對現實的愛恨,好讓積極的發言與表態能夠掩蓋我們那滿腔憤慨、義憤填膺或疲勞過剩的贖罪之心。遺憾的是,當我們付出越來越多心力來關注現實社會、優化藝術的美學語法,但藝術卻從未認真回饋我們的付出。真心換絕情的結果,是藝術圈內層層剝削的預算、甲乙方的不平等、權力結構的角力、資源分配的爭奪、論述話語的華而不實、血汗的代工、寒酸的稿費與人情交換下的勞動薄酬。
那麼,今日的我們該如何重新思量藝術與現實的尺度關係?倘若藝術至今仍然被期許是一把能夠鑿作現實的鐵鎚,那麼我們該如何確切得知應用鐵鎚的輕重緩急?甚至,對於藝術能夠改變現實寄予厚望的我們,是否其實更亟欲看到的是能夠具備強悍傳播力、迫切解決、即時反饋、有積極實用性的「藝術」?藝術在大多時候被任命於「回應現實既有發生事件」或是「創造事件來回應現實」,然而事實上我們一直鮮少以藝術去探問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並從而去預防或延緩危機的發生。於此而言,如何去推測並設想未來危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如何在當下思考藝術可以做什麼,或還能做什麼?
現實的未來:「科技危機」的隱喻
來自未來的災難,勢必少不了科技時代下的工具濫用,及其所有權壟斷的問題。
未來學家庫茲威爾(Ray Kurzweil)在2005年出版《奇點臨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宣稱2045年是機器智慧超越人類智慧的「科技奇點」(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數年前仍然有大多數人認為人機合一、AI威脅人類只是種科幻敘事,然而2022年開放大眾應用的弱人工智慧工具Midjourney和ChatGPT的超速崛起,眾人才猛然一驚、急追直上AI的熱切討論。雖然人類的科技創新頻率究竟是倍數成長抑或是逐漸走緩,至今仍然眾說紛紜;但比起擔憂2045年的人類會被AI吞噬,不如先擔心人類對機器的所作所為與數據訓練,正在對其他人類進行慢性的剝削和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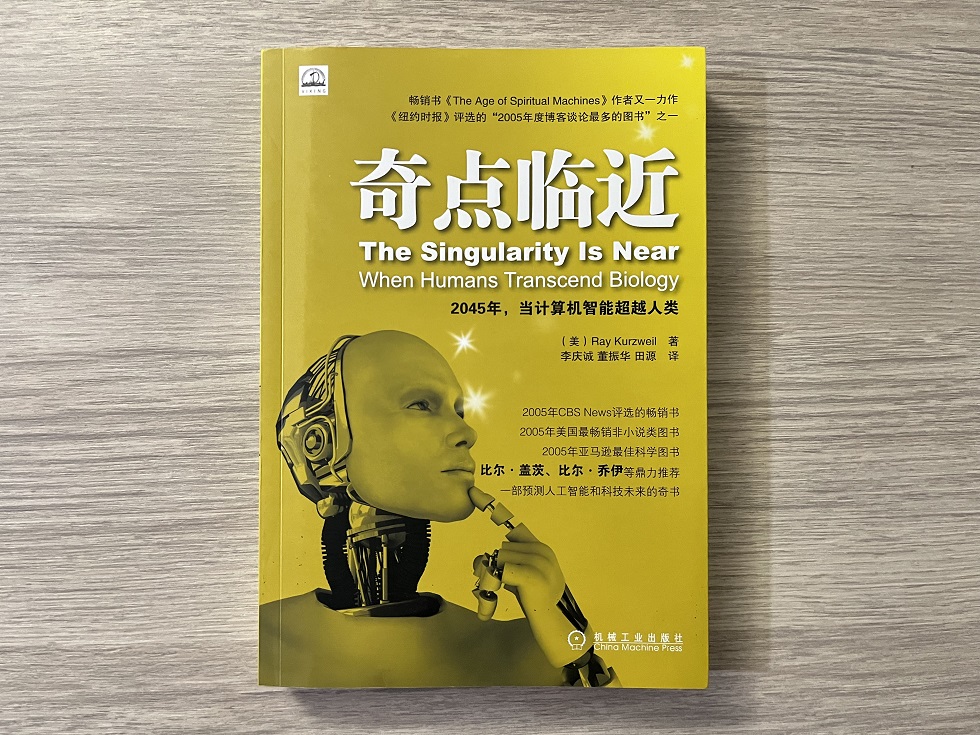
隨著各大科技公司意識到數位內容的價值,紛紛開始暗地裡限制數位工具的研究發表內容、降低數位工具模型的開放性,甚至壓制數據資料庫的訓練。各種大型語言模型(LLM)目前也已被證實存在著許多的不平等與強烈偏見,因為生成式AI系統高度向英語世界傾斜,而非英語使用者的語言模型則因為字元序列長度差異所導致的技術延遲,將極度加深西方與非西方的溝通困難。此外,資料庫中也仍然存在著嚴重失衡的知識分歧,包含像是人種、族群、性別、文化、地方性等階級差異。然而,在改善語言模型之前,從我們每個人身上所搜刮的數據、個資,早已被販賣出去,變成國際政治鬥爭的工具。
所謂的開源都是假的正義,被壟斷的所有權才是真的邪惡。當資料價值被少數人壟斷,就會使得多數人無法共享,並導致價值的再創造性有所缺失。該如何不把數位工具的應用變成誤用、濫用,關乎的其實是我們對數位工具的解放性還能存有多少信任?
同樣是2023年,我們歷經去年對AI如此大幅度進化的嚮往與懼怕。不過,AI帶來的危機絕對不是新科技對人類生活運作傳統的威脅,而是掌權人類對人類他者的壓迫、壟斷與棄絕。以至於,我們再也無法否認,科技危機一直都跟我們所謂的「現實危機」,同在地表上與在人類文明中共存。並且,AI在近年來的加速崛起,更突顯了我們的時代命題:比起區域性或遙遠的事故,唯有當人類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危機,才更有可能真正面對現實問題朝向自身的迫切襲來。
我們對於科技危機的意識遠不及非科技事件,無非是因為科技或數位往往被假定是屬於「虛擬的」、「難以被立即掌握的」,不具有物理向度的事物也更容易被忽視。不過,科技帶來的可能危機與災難,絕對不比土地問題、社會顛簸、政治動盪來得輕微。甚至當科技早已成為每個人的日常現實,我們的警覺心仍然普遍低弱,其中一個關鍵理由不外乎是科技的災難性往往不是突如其來、硬性發生的。當科技全面掌握我們的生活開始,就已然無法杜絕、無可逆轉。故此,該如何延遲科技災難的發生就是人類可以防範之首要任務。恰因為科技危機並非外顯、硬性,延緩災難的軟性工程就有其必要。
行文至此,與其說本文在談「科技危機」,不如說,其實更是在拒斥藝術對既定事件與事實的話語控制,轉而朝向未來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而藝術如何以更積極的研究態度去認真迎戰尚未可知的危機——才是持續保持藝術能動性的關鍵之一。換言之,我們對藝術行為或藝術行動對事後現場的修復、療癒和回應的想像投射,是否只是持續無限鞏固藝術功能的超凡、崇高與神聖?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個國家、環境所無法達成或無能為力的事,需要任命藝術來背負著改善社會的重責大任?
我們對藝術之於現實的行動性的願景和慾望,在科技危機之下都被迫從「立即性」的迷思中覺醒過來——亦恰如此,藝術作品不再是唯一說明現實、現象的保證,反倒是藝術家對未來危機的敏銳度、關懷核心、論述與行動,才是最能夠回應給身處當下時空的我們,最高度相關的預言和提示。
藝術未來學:藝術的未來有提示嗎?
未來學教會我們的,是在數據資料發展時代,我們需要先承認人性致使的科技危機是將至未來的現實困境。不過,我們實則無需繼續抑制科技的發展,反倒是我們該如何直視當下、預言未來危機,試圖讓科技導向「善」的發展,並隨時作出防範與延緩未來危機的準備。
2045年作為科技奇點之年,意指的是人類超越生物學限制並與矽基智慧結合所邁入的「人機合一」紀元,實際上具備正向與樂觀意涵,而非什麼世界末日大限。我更願意將其視為一個隱喻、一個警示鐘上的分段計時,以檢驗我們是否有效延緩惡意全面降臨覆蓋的驗收階段。縱使2045年會因為人類的自私和權力集中而招致科技危機,如同世界和平只是2050年淨零排放那般天方夜譚的癡人夢話,不過倘若我們真的願意努力讓「善」的數據與科技持續長進,就多少還能保有與「惡」制衡的那一丁點能力。
若2045年能夠安然走過劇烈變動且肉身仍然安在,我們不妨相約在2046年,一起在某個可以俯覽地面的咖啡廳,回首細數世界在這二十載內豐盈了什麼、蒼白了哪些。猜猜看我們的共業讓哪些人事物遁入了不可逆的奇點?又有哪些已然絕種或消逝的能被我們重新召喚?那個時候照護著我的幫傭,是來自印尼泗水的堅毅女性還是潛藏在腦神經元中的強人工智慧(Strong AI)呢?而你,還在做藝術創作嗎?我又是否還能寫出一篇宣稱只有我才能寫得出來的文章呢?
本文作者|謝鎮逸
在台馬來西亞人,表演藝術、當代藝術、電影研究者與評論人。現為IATC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理事。畢業於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戲劇與影像系、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現就讀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