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主持:
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所長薛保瑕
與談人:
台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所教授顧世勇
藝評與策展人、台藝大雕塑所客座教授高千惠
師大美術系兼任副教授賴香伶
文化部藝發司司長梁永斐

創作美學脈絡與補助節奏的交織
擔任研究報告撰寫人的顧世勇,從創作美學脈絡出發,提出1980年代國藝會啟動之前至今的台灣當代藝術觀察。他強調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跟國藝會補助不必然有絕對關係,但這樣的回顧仍能提供藝術動態與補助機制演變的對照。
顧世勇認為,歷經1980年代以來的演變,1997年國藝會補助機制進場之時,台灣當代藝術環境已臻成熟。國藝會補助自啟動以來,毋庸置疑對藝術環境扮演著相當有意義的角色。然而,補助機制與藝術家的創作能動性,卻也從此存在著動態關係。

顧世勇認為國藝會補助對於前衛、具實驗精神的創作支持有其成果──國藝會從1997到2014年的122件美術類獲補助案中,以複合媒材與影像裝置為大宗,而諸多藝術家也在國藝會支持下獲得不錯的後續發展;補助仍可能對藝術家創作動能帶來影響:「藝術家過度仰賴國藝會每年兩次的補助節奏,對創作持續力、創作潛能的挖掘與創作節奏的主動性是否影響,是需要關注的。藝術家的創作需要自發性與熱忱,而非以補助來做為創作考量。」顧世勇問道:相對於目前博覽會盛行的市場品味消費,國藝會是否應更堅持人才培育的藝術生產?直面社會結構問題,國藝會若致力於專業前衛藝術家的養成,又是否具備足夠條件來供應養分?他更反思,檢視國藝會對新興私人展演空間的補助,即便貢獻卓著,替代空間也可能因過度仰賴補助,失去固有的邊陲實驗與戰鬥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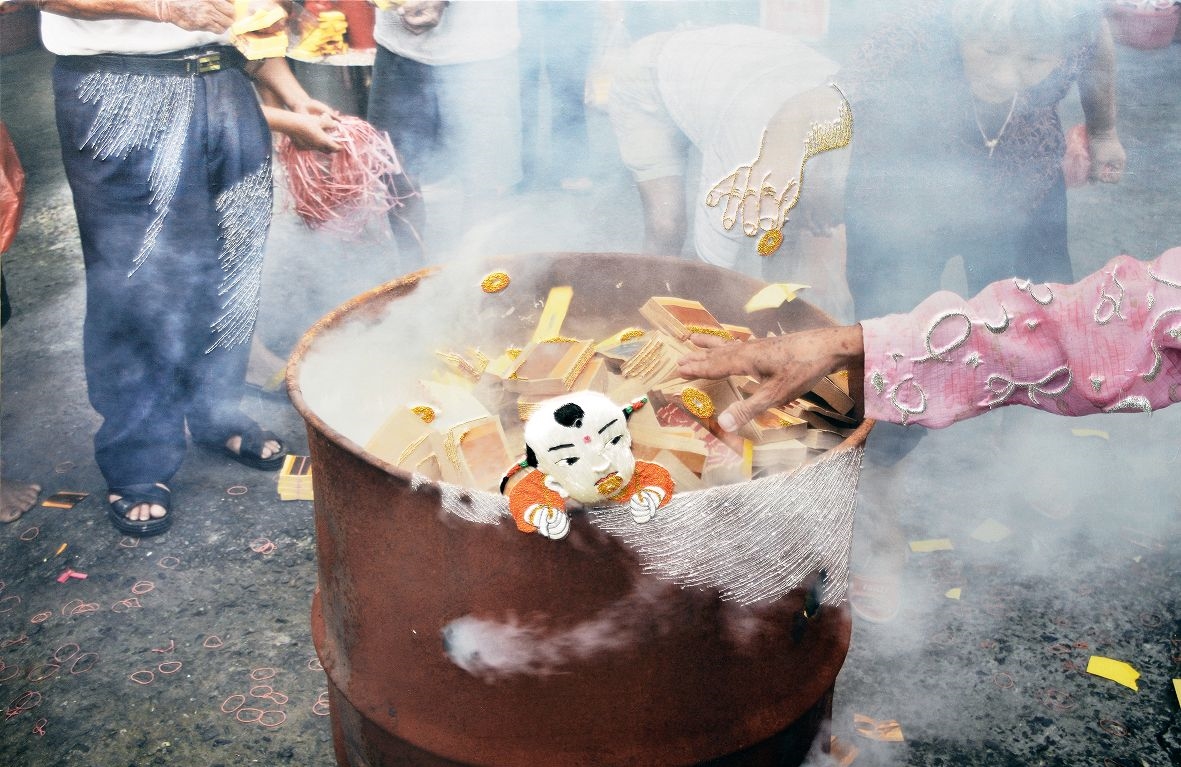
補助機制與藝術生態,是怪獸還是輸送帶?
接續顧世勇以創作美學脈絡的檢視補助機制的角色,藝評與策展人、台藝大雕塑所客座教授高千惠在的研究分享中,則以藝術文化批評角度觀察國藝會20年的回顧與展望。
……我很好奇國藝會是『怪獸』還是『輸送帶』?提到怪獸,是因為國藝會可能對台灣藝壇的導向有相當影響性;第二因為國藝會是資源的來源,對對資源的去向是否有主動性的想法,還是因應評審想法發放,也可能影響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使創作者像探風球一樣進行創作,或想知道藝術到底走到哪個方向了──當代藝術圈常有人在討論現在的趨勢往哪個方向走,對我來說這是蠻大的危機。
高千惠認為,面對台灣當代藝術和國際接軌的「與時俱進」,國藝會做為一個國家文化機制的補助單位,是否可能考量台灣區域美學或國家美學培養的需要?而國藝會參照歐美先例而建立的補助機制,是否適應台灣的體質,在不同民情、藝術家、文化背景下可能產生的異化現象,也需受到批判性的檢視。

高千惠從「名單」發想,補充統計數據所不足以揭露的視角。她認為申請者或評審的「名單」作為表徵,扮演台灣藝壇的諸多角色,背負著不同的文化符號,在國藝會歷年檔案裡,鋪排出諸多想像。
國藝會在視覺藝術介入層面廣泛,幾乎囊括台灣所有藝術生態,在補助機制的運作過程中,也產生藝術工作者因競存狀態而發展出的策略性選項。
高千惠由此觀察出兩種補助結構:「M 型補助」結構與「W型補助」結構。從國藝會大量申請件數、補助件數及類型屬性觀察出的M型結構,顯示國藝會的美術類補助發展出的極端化現象:一頭補助專業資深藝術家,一頭則雨露均霑以少量數額大量補助正在冒出頭的年輕創作者,「在中間的一段、開始有一些自己方向出現的創作者,反而是較辛苦的。」而個人申請範圍的W型跳島式結構的出現,是因為當藝術家或藝術單位熟悉補助申請後,可以多次申請方案,如在申請創作後,再申請展覽空間或國際交流,國藝會在規則上並沒有很大的區辨。其結果,是熟悉補助申請的藝術家漸漸擁有較多機會,而不善企畫書寫的創作者,可能就會慢慢放棄國藝會補助的選擇。

高千惠也觀察,近幾年補助申請者的特定取向漸漸浮現:如在對策展理念的注重下,從社會學、哲學、人類學各種角度介入的展覽呈現,藝術美學可能慢慢被忽略;尤其議題式策展在今日成為主流,在這樣狀況下,藝術創作團隊的分離,市場派、前衛實驗性等創作的區分,都並非健全想法。基於上述,國藝會扮演中介組織,在專業與實驗性的矛盾角色界定中如何調整補助區分?能否思考對於創作能量旺盛的資深、中生代藝術家的支持;也讓實驗性藝術家能繼續延展、創新?這三個方向都是值得繼續思考的。
單一機構的光譜的開展,或是不同組織的多元承擔
主持人薛保瑕回應兩位講者:「補助系統的存在,的確有幫助,可以激勵藝術生態環境有所前進的補助系統,應該有更新的思考。……我在1996年從紐約學成回來,那時念完博士約40歲也不算年輕,可是當時遇到前輩藝術家,卻跟我說:『你們年輕人最好了啦,補助系統都給你!』時光一到我發現我60歲了,中間我發現,當時所講的年輕世代,已經變成台灣的中生代,時光是前進的,但M、W中也有結構性的改變。國藝會一直重於實驗性、新興藝術的樣態,以及具有高度前衛性的角度,來做為專業藝術批判裡面可能覺得被考慮補助的對象──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是否可能有新思考:從新生代進入中生代,是否還可能有補助支援,或是當來到創作高點,使否還有另外補助資源的可能?」
她也回應對替代空間的討論:「我們所謂的實驗性、前衛性是什麼?……早期替代空間和主流、公部門補助切割清楚,獨立自主、不受任何影響,純粹只為自己藝術理念存在──作為一個藝術團體空間,應該保有絕對的自由。但我們逐漸發現更新的複合式替代空間產生,之中交織出定義上跟文化部閒置空間再利用補助目標非常接近謀合的樣態,使的替代空間的方向也在轉型。複合式的空間方向好像蠻活潑的,生活美學概念進入、創意園區概念也進入,融合在一個大個情境之下;但相對下實驗性、前衛性,甚至高度的專業的藝術性,是如何轉型?到底我們在面對轉變時,國藝會的替代空間方案的補助,未來還有什麼可以近一步思考的?」
曾任國藝會獎助組總監的賴香伶也回應,一個機構的發展就像個人生命歷程,面對時間發展,勢必要經過移位、重新定位或轉型。「但是轉型也必須因應更大環境的需求,也就是說,它是否必須將光譜開展為更多元的面向,或者,光鋪的開展其實無法仰賴單一機構──而要在更高的文化部的文化政策下,由更多的機構來承擔這個光譜?他們各有利弊,沒有辦法提供一個明確答案。」
賴香伶也認同國藝會在二十年來從最初臂距原則下,由公部門支持藝術原創的單純目的下的常態補助,直到2004年開始的策略性的補助,歷經不同階段的成長與轉型,尤其在策略性補助更值得肯定:「國藝會一開始是支持原創發表,如科技藝術,或是鼓勵大型展覽製作的策展專案;後來轉向對環境的關注,以及藝術評論、寫作等調節;到最近著重在人才的培育,以及至今國際平台的面向,關照的向度不斷在開展。我認為國藝會的常態與專案補助在這二十年都非常能夠貼近藝術生態的需求,且能前瞻到未來、國際上的趨勢與對話、關注的現象。」

賴香伶認為,在不同階段,國藝會被賦予的責任更大,如果未來國藝會使命開展越來越複雜,是不是還要包裹這麼多責任,還是要藉由更多機構來分擔?再來,面對進駐空總創新基地的評估,國藝會未來也可能擁有更具有行動力、現場性的角色。不同階段角色的轉進,核心價值必須有何轉向?未來專業職能是否能夠或透過與不同單位的合作整合,去因應、支撐更為複合、複雜的使命?要謹守平台角色,還是成為現場,都牽涉到不同的思考與專業。
最後,賴香伶也強調民間資源的引進:「作為民間補助機構,國藝會和民間的距離很親近,有很多民間的資源。但是藝企合作的資源如何被有效運用到國藝會的工作?應該鼓勵藝術優先的影響力(affectiveness)還是效用(effectiveness)?與企業協力共創,而非誰為誰服務,這些是未來可以去思考的。」

在最後的討論中,文化部藝發司司長梁文斐從國家文化政策角度回應,認為除了文化預算的提撥,文化資源重整與跨部門的諮詢,將能促進相關資源的導入。高千惠及顧世勇則在最後反思文化的定義與詮釋:高千惠表示,國藝會從創作端補助建立文化、藝術,連結點在於文化定義的詮釋,國家資源挹注下支持的文化藝術,是否必須是我國文化、在地語彙,更必須思考傳承的議題。顧世勇則回應:「文化不能被當成一種樣板,必須在地栽根。未來新媒體、科技的整合下,是否有新類型(補助項目)的出現,也必須思考。另外,台灣許多角落有沒沒無聞的人在工作,是否能夠發掘在地精神的原生藝術與藝術家,而不是等待他們送審?我期待國藝會能夠更為主動。」薛保瑕則高度期待國藝會提出對補助資料的運用研究:「台灣藝術家累積了20年的資料,是我們最重要的資產。台灣藝術家的藝術成果,建構了台灣在特定時代中的美學界面,這個介面有了藝術實踐,還有藝術家思維的成形。有了這樣的研究,面對國際,我們才有更好的準備。」
下載完整報告:
【美術篇】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機制/顧世勇
【美術篇】是怪獸,還是輸送帶?名單,作為官方機制與民間藝術生態的關係索引/高千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