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23年遇見的最令我驚喜的作品是張之洲的攝影書《五個攝影師》(Five Photographers)。他虛構了五位風格各異的攝影師,看起來就真的像是不同人所拍攝。但是重點是在於他們的「自述」都非常的諷刺。我在廈門「三影堂」駐村的時候看到這本書,有一種非常複雜的感受,一方面因為疫情結束、出國駐村等等原因,都讓我覺得頗為振奮。但是另一方面我卻在這樣一個專業的攝影藝術機構當中,看到這樣一個虛無的文字,好像是對於此時的我的一種諷刺。
Q從來不想承認自己攝影師的身份,他堅持認為自己是個藝術家,並且是當代的。他對藝術史充滿興趣,總是泡在網上看大師們的作品照片。至於他自己的作品,他不斷地想尋求先鋒和突破,可經過幾次三番的嘗試之後,他發現他拍的東西總是和他看過的那些藝術家們的作品有這樣或那樣的相似,他為此抓狂,時不時地感嘆這世上已經不存在新大陸了,能被創作的都已經被創作了,當他意識到這個想法本身也已經被人喊爛了的時候,就開始沮喪了。但他沒有放棄,仍在尋找突破之法。
後來他開始熱衷於購買理論書籍,但買回來卻看不下去(至多看一半),他最多的閱讀是在網上看那些被引用的哲學片斷,有時他甚至只看書名就覺著懂了一半。這樣的閱讀多了起來,他竟也似乎能對什麼都發表些意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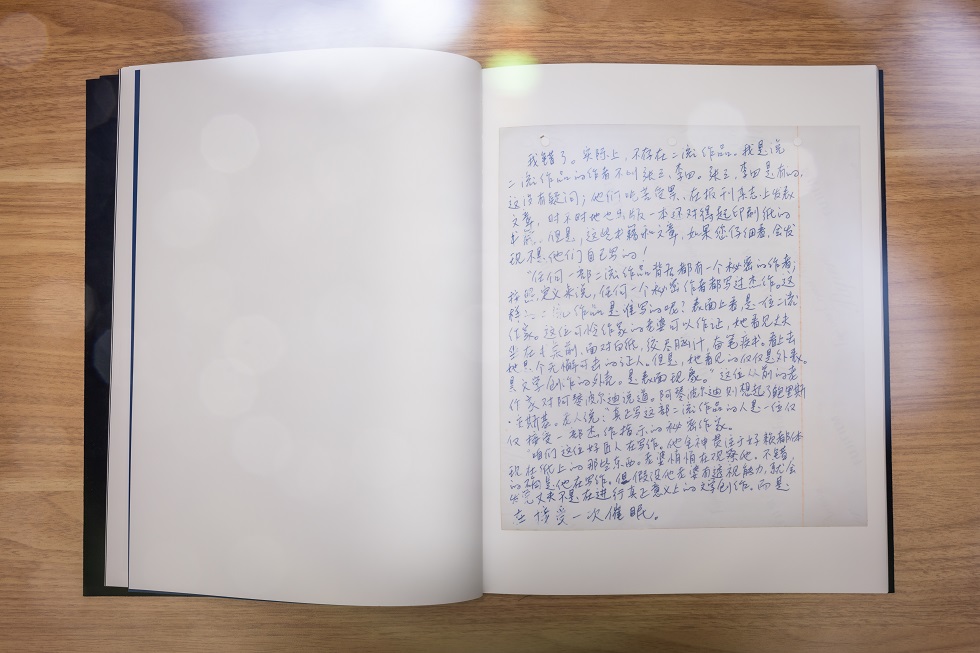
其實這種對於攝影與藝術家的嘲諷並不少見,從桑塔格的《論攝影》到卡爾維諾的〈攝影師奇遇記〉都可見。它可以分成兩種層次。一種是對於作為藝術家感到虛無。我們學藝術到一個程度多少都會覺得我們實際上遠離了現實,因為藝術實很難說有什麼的用途(不論對於社會或是對自己都是如此),但是藝術在現代主義之後被推崇為一個社會之上如此特別的存在,這導致創作者常常陷入一種自我矛盾的心境。這個問題又因為當代藝術強調研究、論述的取向而變得更加嚴重。有一本書叫做《Talking Art: The Culture of Practice and the Practice of Culture in MFA Education》,裡面描述美國藝術學院有一種「嘴藝術」的現象。譬如評圖的時候要講自己的作品,展覽的時候要寫很長的創作自述,或是每個藝術家都把自己想像成研究者,進行一個個研究計畫。當創作者可以掌握這種學術語境時,論述作為創作並不是問題,我們早就告別了那個藝術一定要是實體的時代。但是當創作者無法掌握學術語境時,就會覺得學習、使用這些文字非常的心虛,好像自己只是裝一個(當代的)樣子。
第二個層次是對於攝影本身的虛無。藝術本來就不太實際了,可是攝影又特別給人一種不踏實的感覺。對於任何喜愛攝影的人只要他願意,他不僅可以快速的生產出看起來像是藝術的作品,而且還能夠透過攝影聯繫到各種課題,譬如個人生命、歷史、社會議題,乃至於抽象的哲學思考。按理說這應該讓攝影師覺得非常的充實,可是正好相反。因為攝影快速的讓我們從一個業餘的愛好者成為了一個類藝術家——儲備了大量的照片與藝術知識,所以我們會在某一個時間點感到慌張。這些照片真的跟我有關係嗎?這些深刻的藝術問題真的是我有興趣的嗎?我們會發現真相是,我們不僅沒有辦法靠攝影藝術維生,同時我們也發現在知識上攝影關心的問題也與當代藝術距離遙遠。


這裡進一步的問題是,攝影在藝術上失去了力量。表面上,攝影理所當然是藝術,至少我們都同意桑塔格的觀點,攝影是一種媒介,它可以是藝術也可以不是藝術。但是實際上攝影面臨著當代藝術理論嚴厲的批判。有一個玩笑就是,最快摧毀一個人對攝影的熱情,就是把《論攝影》、《攝影的哲學思考》與《再現之重》看一遍。這三本書都在講照片在社會之中如何運作,而且常常是負面的。《論攝影》不用說,在桑塔格口中,照片就是「獵奇、窺伺、誘惑、暴力、雄性、獨斷、貪婪、侵略性、怪異、濫情、昇華的謀殺、最無法拒斥的心靈汙染、遠距離的強暴」。《攝影的哲學思考》對於攝影也沒有好話。它基本上從傳播學的立場出發,談論看似中性的攝影(器械)技術如何潛藏了各種意識型態。這個立場比桑塔格更極端,因為只要使用這個器械,你幾乎就是不自由的(唯一的解脫,就是你認知到這種不自由)。《再現之重》比較像是以歷史學的方式研究照片作為一種物質如何在社會之中流通,如何被機構利用,如何被人所接受。它強調攝影應該從攝影與知識、權力的關係,也就是傅柯所說的真理體制著手,而非研究攝影本質。
上述觀點顯然是一種左翼的立場,認為後者來自於一種神祕的、包藏禍心的、對於真實過度天真的心態。而他們的理想是揭露影像的問題,然後用一種布迪厄式的社會學視角研究照片在社會之中實際的作用。基於這種觀點所見的攝影必定是有毒的,或者我們可以說是虛無的。而張之洲這個作品很坦誠地把這樣的處境傳達出來。它背後所隱藏的是一種對於圖像的悲觀。因為如果所有的圖像背後都有某種權力的運作,那建立在影像上面的攝影充其量只能作為一種反諷,而沒有本身的價值。當作者虛構五位追求各種風格的攝影師更能夠訴說這件事,作者彷彿在說我們根本不是自己想拍什麼,而是一種關於攝影的套路讓我們想要這樣拍。


但是這也不是我真正喜愛這個作品的原因。我之所以喜愛這個作品是因為這個作品透過一種虛無成為了作品。說到底攝影一開始吸引藝術家的原因,並不是攝影很藝術,而是攝影不藝術。從1935年的紀實與反圖像攝影、班雅明的靈光消逝、羅蘭巴特的刺點,乃至於1960至1970的觀念藝術,它們彷彿都在宣稱攝影的直接、自動、淺白、可複製等等不是藝術的特徵,正是攝影最為藝術的地方。事實上還有什麼比起一個人精心製作一本嘲弄攝影的攝影集這件事更符合這種精神。它彷彿在說我們誤打誤撞的走上了藝術的道路,但是我們發現我們在其中迷了路,於是我們為這個迷路的狀態重新描繪一幅地圖。它並不能指引我們身在何處,而是告訴我們不在任何地方——就像照片一樣。
本文作者|汪正翔
1981年生,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後赴美攻讀藝術攝影。創作以觀念/行為攝影為主。目前看得見,會按快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