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日本作家真藤順丈在其初啼試聲即成代表的小說《地圖男》裡,描繪「地圖男」形象:他緩緩走在人行道,胸前抱著攤開的官方地圖,一副看不見周遭事物的表情,獨自一人,口中念著密密麻麻的故事。
我著迷於「地圖男」的形象。具體來說,是他那種「沒有目的地,而是在找一個地方」而游移,或者,在人們制定好的地圖上遊走的狀態。
2014年,面對台灣與香港的政治運動的焦慮,我暫且完成碩士論文《鏡縫拾荒——展演地圖:從巴黎公社到飛夢社區》(由藝評人林于竝、陳雅萍指導)。這部長達33萬餘字、近500頁的書寫,探究自法國大革命以降,到今天街頭出現的公民不服從運動,過程中,「藝術」展演曾面臨何種可能與消逝?我認為這是一種藝術歷史的嘗試。這份帶有散文性質的學術論文是我暫且封筆藝術評論,也是我20餘歲階段的最後一篇藝術批評。此後,我的行動轉向,開始朝往「歷史交換」的創作、與後來的社區實踐與族裔關懷。
這篇文章,鎖定於前者。

一、改版A:為誰而生的文字?
對我來說:「改版」,就得看重「為何行動」的動態過程。
十年來(2009–2019),有些幸運機會,促使我曾有相當時間待在蘭嶼、桃園、台南、港澳、河內、金邊、望加錫(Makassar)、新加坡、墨西哥市、烏蘭巴托與代芬特爾(Deventer)等城鎮。這些地方常因報導工作、參與(策)展覽、駐村研究、受邀評論或社區研究而前往。坦白說,我不能說明這些過程中,哪些作品該「改版」?
它們確確實實為某些地方的政治、經濟與歷史狀況而生。
暫離「藝術創作工作」的幾年歲月,宣示我的名字在都會「藝文圈」間消失了。為了反思藝術做為社會實踐的可能性,我前往以東南亞移工與新住民議題為主的《四方報》,擔任記者與專案經理;及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的社區營造中心,負責藝術活動等規劃。
甫到報社時,即受同事叮嚀:「記得文字要讓各國媽媽們翻譯,轉化成令人理解的資訊吧。」這般建議對我這種常被詬病用字艱澀的慣性評論者來說,等於是全新考驗。累積些許報導經驗後,2016年,我向竹圍工作室申請成為駐村藝術家,遂以「記錄者」身分回到藝文場域,重新開啟不僅社區民眾讀得懂、及擴充「社區報」藝術意義的「樹梅坑溪.阮ㄟ報」,策劃了正式停刊前的第23期1,也意外協助實踐了蕭麗虹老師所期盼的--這份報刊應記錄在地東南亞住民想述說的心聲。
二、改版B:為誰而生的藝術創作?
2017年,我接連參與「近未來的交陪: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與印尼「望加錫雙年展」(Makassar Biennale)的創作邀約。前後,我陸續完成三篇有關如何連結台灣早期東南亞史考察與荷蘭殖民時期的都市規劃及市民劇場等研究。
我對「歷史」極感興趣。在近年的藝術生涯中(若有的話),「為誰而生的藝術創作」的改版行動,意味著讓藝術作品為少數人的「記憶」發聲,甚至是我反思「問題化」的藝術實踐旨趣。
我試將台南與印尼蘇拉威西島的望加錫歷史「並置」,發現了相互連結且被遺忘的女性故事,並以1655至1657年嫁來台南的望加錫婦女茱莉安娜(Julianna)與安娜(Anna)的肖像進行發想。

2017年2月的「交陪」展裡,我從荷蘭萊登大學圖庫中,找尋最古老的望加錫照片。圖庫裡包含婚姻、荷蘭家庭、蘇丹陵墓和風景等。照片乘載記憶,使那些人、事、物「曾在」。照片是我們當今能推敲視覺記憶的最前線:我們目擊今百餘年前的人物故事,而歷史與傳統又是層層積累,透過這些視覺資料,我們得以繼續推敲「更早以前」的景觀。
「交陪展」所在的台南蕭壠,數百年前是荷蘭殖民時期重要的平埔族部落。而望加錫婦女與班達島民的形象在此重現,也為這些無論是幸福嫁來的女子、抑或客死異鄉的奴工,盡給予歷史上的記憶。這批繪畫屬於「這裡」(台南),以至於該年11月的望加錫雙年展,我並未帶著「安娜」與「茱莉安娜」肖像前往原鄉。對我而言,台灣終究是兩位女子選擇的歸屬。
這段期間,我在菲律賓歷史文獻中,找到曾駐居基隆和平島的西班牙傳教士安赫列士(Fray Juan de los Angeles)遭荷蘭軍隊驅趕後,於望加錫寫成的〈Formosa Lost to Spain〉(1642)。這是一篇待人翻譯、記錄福爾摩沙(的西班牙人)戰敗原因的重要文獻。這位神父以高超記憶力,清楚記載發生於台灣本土的西荷戰爭,包括軍隊、人數、軍官名,及當時曾在北海岸的堡壘地景(如修道院、麵粉廠和倉庫等)。
我的創作主旨來自兩地的古老記憶,以及海洋時代的反身思考。然而,該系列創作在台灣藝壇未能帶來討論,反倒在印尼望加錫雙年展期間引起大學師生的歷史反省(事實上台灣藝壇或許也對望加錫雙年展不感興趣):如何以某種藝術創作型態,讓兩位望加錫婦女的故事「留」在台南,及把西班牙神父離開台灣的最後印象,在數百年後帶入望加錫展覽現場?
交換記憶的物質性與想像性是什麼?望加錫雙年展基金會邀集該地木工,前往港口貨櫃區或菜市場蒐集舊木材,為我打造數個航海時代船上的小型木箱,裡面裝滿丁香粉(cengkih)、米糠(sekam)和海砂,讓觀者親自用手撥開海砂,聞到米糠和丁香味,慢慢找到我創作的繪畫。這些「無歷史的人」難現於台灣史,並且反映了望加錫本地海洋歷史的重構,因此更有想像力。2

三、改版C:朝向大眾的文化再造工程?
2018年8月起,我陸續參與「IS/IN LAND:台蒙當代藝術游牧計畫」。我首先重返「母親們」身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歷史敘事;二來透過創作,在烏蘭巴托建構蒙古現、當代城鄉移民的故事。
即便台、蒙兩地曾分屬不同冷戰陣營,我仍試圖創造一段勞動者的共同敘事。
我以母親勞動故事為基礎:70年代後的台北,矗立了不少美國和日本的企業及工廠。當年在美國扶持的經濟環境下,紡織、食品罐頭、電子業已成為島上最出名的外銷貨品。而她跟無數女工一樣,暫離偏遠山村,靠著努力當上美國工廠的領班,於鮮白、乾淨的日光燈下,裝配無數的電視機。
我的母親看影像、試聲音,耳邊傳來美軍電台裡的英文歌,這些音樂是當時唯一的娛樂。40年後,我挖開電視機,電路板一如往常般的像座陌生的城市。
會有那麼一天,搭著火車離開充滿電路板的工廠,回到山村的家人身邊,是她最殷勤的期盼。

蒙古駐地創作期間,我挑選蒙古每個時期「20年代」的代表事件,藉此反思不同年代面臨國家與國家中間的妥協、征服、被殖民、革命,及至即將到來的2020年,嘗試直視冷戰時期到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分工與城鄉差距等問題。
我從古老的戈壁岩石雕刻尋找創作靈感,回首每個時期的20年代,蒙古人民在時間與勞動變革中,層層鋪疊於未知的歷史向度上,過程中如何彰顯或隱藏?3
四、小結:迎向有時代生命的藝術創作
「為誰而生的文字?」、「為誰而生的藝術創作?」、「朝向大眾的文化再造工程?」十年來,從記者、社區營造工作者到進入台大城鄉所進修的自我詰問,這三個問題,或許使我從純粹藝術創作的身分,持續更換、累積自身生命經驗的豐富度。這些嘗試持續變動著,我也清楚上述的探究過程,意義多過作品自身,因地、因時而再三改版。
舉例來說:我受惠於澤蒙.戴維絲(Nathalie Zemon Davis)《馬丁.蓋赫歸來記》(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的方法啟迪。這名當代歷史學家透過大量日誌、地圖、寓言、歌謠、戲劇、法律契約、訟詞等方式,以虛構卻又最接近真實的摹寫,重說16世紀法國平民「蓋赫」的傳奇故事。
戴維絲影響了我,換言之,必須透過大量的視覺圖像、地圖、歷史資訊和日誌,建構360年前望加錫女人安娜、茱莉安娜,與從基隆前往望加錫的西班牙傳教士安赫列士「所看過」的世/視界;而台北與烏蘭巴托的交換展,則源於「真實」的召喚:來自母親訪談、蒙古本地的詩集及時事評論,將記憶建構成某種「可見」的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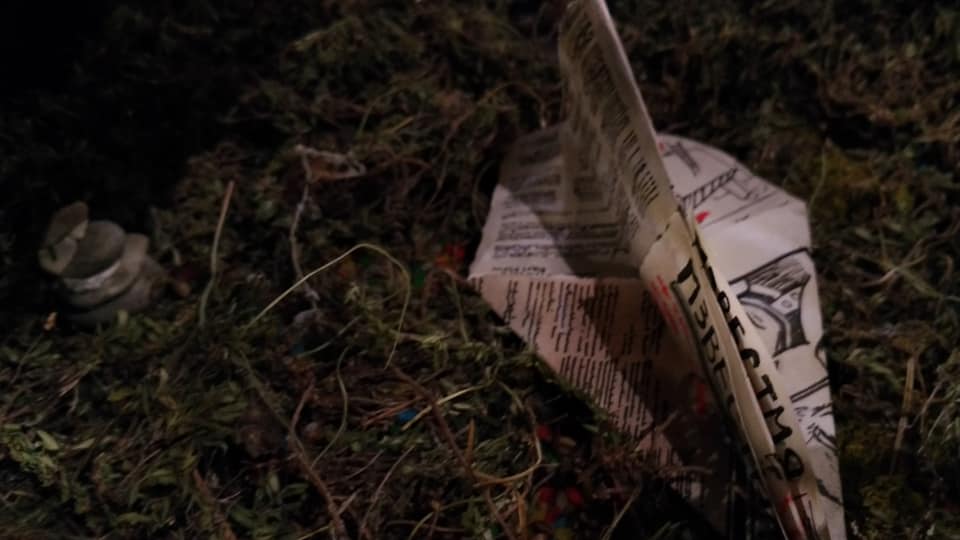
我的創作並不朝向特定目的,而是尋找/定錨一個暫時性的地方,讓某些人說話。
藝術協助我們建構歷史、述說故事:這些微小人物的歷史不該遺忘,畢竟我們在新世紀的藝術思考上反轉歷史。而歷史並非阻礙我們現狀,或叫人一味追尋過去,它幫助我們剷除腳下的絆腳石,驅動人們前進。
註1|見竹圍工作室相關網頁;或林正尉(2019),〈半報半“X”:當「藝術家」遇見「社區報」…〉。
註2|參見《幸福歲月:無歷史者的回歸》創作論述。
註3|參見《Re-rootness-ia: From Taipei to Ulaanbaatar City 2018》創作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