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劇場/表演藝術演出是在製造每一個不可複製的「當下」。
作為劇評人,所書寫的無論該被歸類於「評論」或是「紀錄」,多半是以演出當下為原則。或將劇評視為「創作」後的「再創作」,可被認為是種「延長」那個當下的作法。經過書寫累積後,我開始思考如何串連當下構成脈絡,並將展演的論述置於更長、更大的結構裡──其中,涉及「橫向」的生態、文化、社會等發生語境,以及「縱向」的人類或劇場發展史。以我的書寫來說,因研究基礎,對國光劇團、當代傳奇劇場的作品,多能進行相對脈絡化的評論書寫。較短時間的對照,則如〈劇場文本的行旅痕跡《行過洛津》〉針對作品於2017年松菸版、2018年黑盒子版間的改動;而〈問了「我是誰?」之後《悟空》〉、〈民主政治與娛樂遊戲的互為替身《山高流水之空中》〉則在同一演出的不同場次裡凸顯其獨立與連結;至於,亦有針對單一創作者,如丁家偉、陳煜典等,接合不同作品的時間點與創作概念來形成軸線。
但,這樣的書寫不只有時間、資源等的分配與拿捏,更有「機緣」問題──過去的時間就此過去,錯過的現在就此錯過。甚至,能否重建作品脈絡的時間性?以及重現製作過程與權衡?
於2018年11月正式上線的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已完成2013年至2017年「常態補助」、「專案補助」、「國際文化交流」等補助成果資料的彙整,著實提供建構可能。因此,我將以「戲劇(曲)」為搜尋類型、用「移動」為思考脈絡嘗試回應,也延伸提問。

縱向的回溯:創作/創作者的原初樣貌
劇場創作與創作者培育,仰賴補助資源多時,而國藝會在文化政策轉型的過程裡越發重要。當我們閱覽「補助成果檔案庫」的分類1時,大致可勾勒創作者過往的創作軌跡,亦能藉由他/他們提案的命名去窺探作品原初的樣貌與構想,再對照最後的演出狀態與成果報告。
暫先鎖定「常態補助成果」部分,可選擇申請類別,包含文學、視覺藝術、音樂、舞蹈、戲劇(曲)、文化資產、視聽媒體藝術、藝文環境與發展,再進一步縮小範圍,選擇年度、項目等──其中,我想以「演出」與「創作」這兩個項目來回應「縱向的回溯」。
舉例來說,2017年9月在竹圍工作室首演的身聲劇場《春釘》,是以《我的身體還有拔不出的春天的釘子》為名獲得2017年第一期常態補助。其以詩人海子〈我感到魅惑〉的詩句形成意象,用創作者的身體經驗與小說家史鐵生的作品、生命歷程對話。到了作品演出時,被簡化為「春釘」。原先暴露於名稱的身體意象相對減弱,其取捨表現了什麼?申請案撰寫與作品完成間有何距離?或者,各有追求的目標與想法?同時,身聲劇場於隔年(2018)又以《春釘─告別作者》為名續寫,命名更凸顯與原作的脫離,於是最終目標為創作者的個體經驗與生命情感嗎?從創作命名到呈現的核心移動,是在回溯裡可被觸發的。更有意思的是,在「創作」這個項目裡獲得補助的「劇本創作計畫」。除可提早獲得劇本資訊或內容,如趙雪君《卞玉京》(2017)、李胤賢《水淹陳塘》(2016)等;再者,獲得演出機會的劇本占了多少比例?劇本創作與舞台呈現的距離與差距有多遠?能否有更精確的統計加以呈現與分析?
另外,在「補助成果檔案庫」裡特別整理的「專題資料庫」,已有「國人作曲專題」與「新人新視野專題」,是在結構、編排、瀏覽模式上最為完整者。以「新人新視野專題」來說,更收錄統計圖表與研究專文供給查閱,並以「人」作為資料庫的呈現方式。我們可以通過點選曾獲補助的創作者頭像,進入頁面閱覽創作者的簡歷(包含學歷、經歷、個人作品等)以及連絡方式。其所提供的功能不只是「舊有資料」的檢索與留存,更試圖提供管道,構成「人才資料庫」的效用。不僅提供了創作者的回溯關係,其系統畫面呈現頭像的拼貼,也繪製出一幅世代的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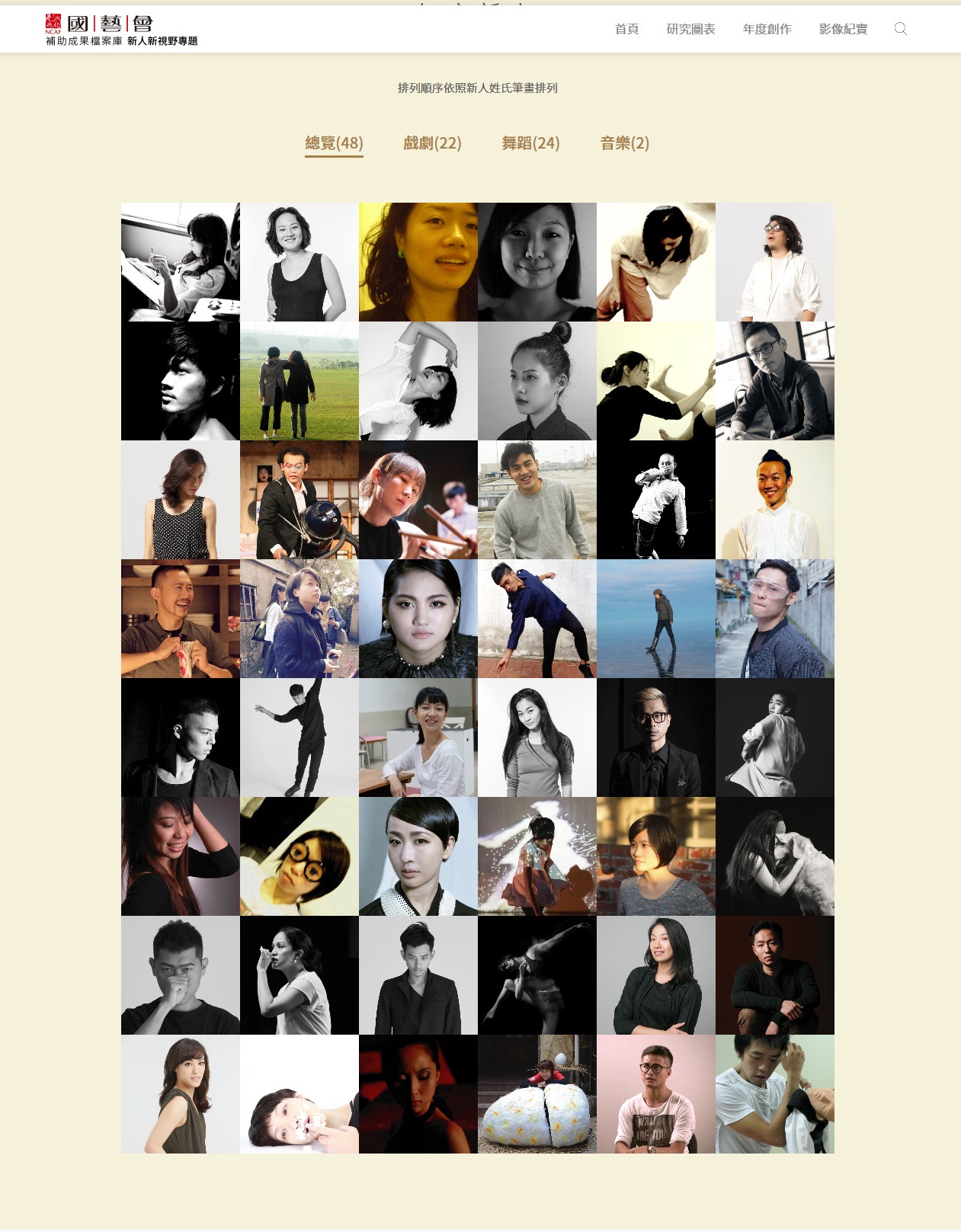
時空的移動:發展脈絡、巡演軌跡的補充與反思
回溯不只是一種單向的觀看,同時也延伸出創作軌跡與場域即景。
於此,編劇詹傑是有代表性的個案。除創作計畫通過數量高,更在於劇本創作到演出的連結程度。以《白色說書人》(2017)來說,分別取得「《白色說書人──我的嘛吉獄友馬克廖・添丁》劇本創作計畫」(2016年第二期)與「白色說書人──我的嘛吉獄友馬克廖・添丁」(演出計畫,2017年第一期),順利於2017年10月於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首演,並巡演台南藝術節(2018)、台灣戲曲藝術節(2019)。於是,正式演出所刪去的副標「我的嘛吉獄友馬克廖・添丁」代表了什麼?另外,其以白色恐怖為材,通過不同的補助類型進行田野調查、獲取資源,建成「創作─演出」的脈絡,何以呈現補助的受惠與實踐的接合過程?2

以一個劇評人的角度來看,「補助成果檔案庫」最大的幫助是協助填補與完成創作者/劇團/作品的移動軌跡,包含巡演間的創作變形(不同場館、不同年份等)、創作者的作品發展等,在文字紀錄之餘亦有影像,雖無法重現,至少補充了縱軸線與橫軸線的部分評論脈絡。例如:我目前想完成的缺漏填補,是在評論兩版《行過洛津》時,因時間因素無法觀看導演陳煜典在兩版間完成的另一個作品《阿依施拉》(2017);那麼,藉資料庫是否能夠更完整勾勒出創作者的脈絡呢?會否這個作品實質影響了第二版的創作呢?
此外,可延伸到「取得資源與完成作品間的關係」。
不分劇團組織大小,巡演成行仍多半與補助挹注息息相關。以2017年為檢索範圍,包含台南人劇團《一家之魂》的台南巡演(2017年第一期)、阮劇團X流山兒★事務所《馬克白Paint it Black!》台中巡演(2017年第一期)、四把椅子劇團《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台北場演出(2017年第二期)等。看似普遍化的現象裡,我所想的是「票房與補助間的互動與運作關係」。也就是說,這些作品的巡演,到底是地方文化資源的平均分配?票房的支撐?還是補助獲取的效應?甚至,是為了符合其他補助案的需求,必須有巡演的場次為業績?進一步地,可延伸到創作團隊「以案養案」的過程,能否通過不同補助案的交叉比對進行分析?不過,這部分的探查是這個資料庫目前較弱的部分,尚須有關鍵字的檢索功能,或是更精細的索引系統3,才能夠有更深入的分析報告。
另一方面,能否看到在補助案「之外」發展的創作可能?也就是,溢出這條移動軌跡外的創作如何被發生?生存策略與模式又是如何?這也是我無法迴避的追問──關於當代的創作生態與結構。
最後,劇評人與創作者間的互動,能否通過「補助成果檔案庫」的建置產生另一種關係與對話,而讓這些資料不只是死板、扁平的保存,能夠在「被使用」的過程裡檢視「使用」(這些補助資源、這個資料庫)的意義,是我以「移動」為角度來閱讀資料庫、摸索創作/創作者的軌跡(不管是縱向的順行或逆轉,或是橫向的空間置換)持續思索的。

註1|「補助成果檔案庫」依國藝會的補助業務及基準,於頁面分「常態補助成果」、「專案補助成果」、「國際文化交流(出國)」提供成果分類、分項瀏覽。
註2|國藝會承辦人說明,重新改版建置的「補助成果檔案庫」在設計上已於成果頁面增設「相關成果」、「成果追縱」等資訊,以提供使用者進一步瀏覽其他相關聯的獲補助計畫,及相關補助計畫成果的後續發展資訊。
註3|國藝會承辦人說明,補助成果資料庫現階段提供輸入「計畫名稱」、「獲補助者」進行搜尋,及各筆「成果摘要」欄位內容的全文搜索功能。自2018年起由獲補助者於繳交成果時提供該筆計畫的「關鍵字」,作為檔案庫「關鍵字」設定與標籤顯示,並預計於2019年底前提供包含附件檔案的完整全文搜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