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今天是2021年9月12號。距離5月中旬猛然到來的三級警戒,剛好要四個月了。
從疫情急速上升,面對所有的突然,在家工作,演出取消,到開始可以工作,影片拍攝可以進行,可以小規模的走回劇場,然後,路上又開始塞車了。
昨日的確診人數是,零人。一查有點驚訝。幾個突發的本土案例,才讓大家神經又有點緊繃。
我又開始在想(其實是擔心),我的VR影片《霧中》週二要在台北電影節開賣,到底能否順利上演?我在想,所有的團隊此刻都分享著一樣的擔心。
我的團隊「狠劇場」,作為一個以國際發展為核心之一的團隊,本來有三個國際共製計畫正在不同階段進行。這疫情讓我們在去年3月打帶跑的在澳洲疫情正要爆發當週演完《虛擬親密》首演,並在10月透過和澳洲導演遠端連線的方式完成了台灣的演出。而去年8月本來要在荷蘭首演的《城市之臉》,也在種種變化下,從全部線上、轉成了在兩地劇場相互連線的階段呈現。直到此刻,我們仍在持續為這個作品思考嘗試著轉換創作展演形式的可能。在去年台灣疫情還算穩定時,我們運用了劇場因防疫而多出來的空檔,在劇場中拍攝了VR作品《霧中》。今年的這波疫情,則讓狠劇場本年度唯一的一檔實體演出《霧中.凝視》延至明年了。

我們真有那麼agile?
agile
adjective
敏捷的,靈活的
昨天我收到在加拿大一個音像藝術節展會(也是一種月老平台)認識的一個藝術中心總監的回信,信末她寫道:
We all miss travelling…. That said, people have become quite agile in working across multiple channels around the world.(我們都很想念旅行……。不過,人們已經變得可以頗為靈活地在世界上多元的頻道上工作。)
我去查了agile,確認跟我印象中的意思一樣。然後我在想,是呀,我們這麼努力的敏捷、靈活的變化著。我們好像學習到了日子還是會過下去,整個世界都在高唱著劇場中亙古的那句「The show must go on!」
當然我也在想,我們根本沒有那麼agile。然後我對著「在多元的頻道(渠道)上工作」這句話有點苦笑了一下。
好像出於某種求生反應一般,隨著三級警戒開始,隨著本來要在台北藝術節演出的《霧中.凝視》延期,(除了一兩個之前就答應了的)我奮不顧身地跳上了一個個國內外的線上講座。看似好棒好厲害的表面之下,其實是死馬當活馬醫的奮力一搏,是劇團補助可能受到影響的擔心,是渴望與他人連結,也可能是害怕消失的恐懼。

於是過去這四個月中,我跟著思劇團去了東南亞講酷兒作品、去了洛杉磯台灣書院跟西岸藝術聯盟(WAA)聊線上駐村的種種可能、去了巴黎新影像藝術節(NewImages Festival)聊XR的生態圈外加一場30分鐘的一對一媒合(相親)、去了紐約參與紐約市立大學席格中心(Segal Center)以24小時連線世界劇場工作者聲援印度疫情的活動、去了愛丁堡談數位和劇場的關係;也去了香港歌德學院的長期線上共製平台,並三不五時和香港、首爾、上海、柏林、慕尼黑的誰和誰相遇,當然還去了這平台的成員們在Gather Town上創建的「Goethe Town」(歌德城)。然後去了加拿大的MUTEK音像藝術節,使用Swapcard這個平台再相親一遍。
這一切的高峰或許就是上週的威尼斯影展,包含一場在文策院攝影棚預錄的論壇、一場和威尼斯現場的連線,更在半夜11點戴上VR頭顯裝置、打開VRChat軟體,站上虛擬舞台分享自己的作品,最後再來個虛擬紅毯照。



這連滾帶爬的一切帶來了什麼
每一場的線上講座、活動、一對一的媒合,準備起來都是一場巨大的工程。除了永遠要不斷產出新的、份量和內容合宜的簡報檔案,語言還是卡在第一關,可以講英文和可以深度的以英文知性地論述還是有很大的距離。不論如何準備,總在結束之後冒出剛剛應該怎麼說會更好的各種給自己的筆記,彷彿自己就擔任著自己的虎媽(Tiger Mom)。完全沒有準備的即興、和完全寫好稿子的過度準備,都還是提醒著自己:我還太淺。
每場講座都有預先的會議,讓大家認識彼此並且順一下流程;正式開始前更要測試技術問題,更新太快的會議軟體有時反而會扯你後腿。頭幾次,當正式開講、所有人都關至靜音時,突然就進入一種絕然的空無,究竟要拉起什麼樣的能量自說自唱,在幾乎沒有回應、甚至也看不到觀眾的情況下,說真的,有時候連斷線了都可能不知道。這一場場不論是半夜、凌晨還是早上、傍晚,連線中的熱情與感謝,總會在斷線後,讓人有種靈肉分離的感覺。一陣空虛的茫然總在這樣的時刻悄悄滲入。
原本到了這個時候,(讀到這裡的你)可能會稍有期待,(看了這麼久的絮絮叨叨)應該來個啟發人心的微言大義。這所有連滾帶爬的一切到底帶給了我些什麼,我學到了什麼,我這個角色有什麼改變?我又有什麼可以與大家分享的最嶄新、最當下的想法?
但好像沒有。
我等了又等、想了又想,我發現我還在連滾帶爬,甚至還帶點連環炮的爆炸著。一時半刻還難好好站起身,好好走路。說是疫情導致暫停了兩三個月的後作用力也好,也可能是它帶出了人人心中對事情永遠都有「變化的可能」的焦慮。即便知道自己和真的面對疾病和生存的人群相較,已是屬於極為幸福的。
不過,我知道這場網路壯遊沒有白走,雖然此刻還沒有被消化完全,它還是扎實的在心裡身上記下來了些什麼。


一個人、但又不只如此的網路壯遊
我在不同的線上活動中學習到,在網路平台上更應該持續應用各種多元共融的介紹與表達,如自己的人稱代名詞(he, she, they),對自己的畫面的口語描述(黑短髮、戴眼鏡並且在一個白色的背景前),甚或是land acknowledgement(領土確認)。更重要的是,我盡可能地把這些用詞,帶入本來沒有相關安排的單位和講座上。我也發現有更多的網路講座利用這些平台本身科技的可能,提供即時生成字幕、或多語翻譯。這些形式固然在實體的場合多少都有看到,但在以網路平台、螢幕為媒介的狀態下,我看到了許多使用者表達對這些用詞、字幕的感謝。我更難以想像,若不是因著疫情,人們以超快速的方式跳上網路平台,我(們)怎麼有可能與這麼遙遠的人們、甚至不便出門的人們有所連結?或許,就像是老諺語提到的:「當上天關了一扇門時,會為你開一扇窗。」當人們斷了近距離的連結時,遙遠的連結就會漸漸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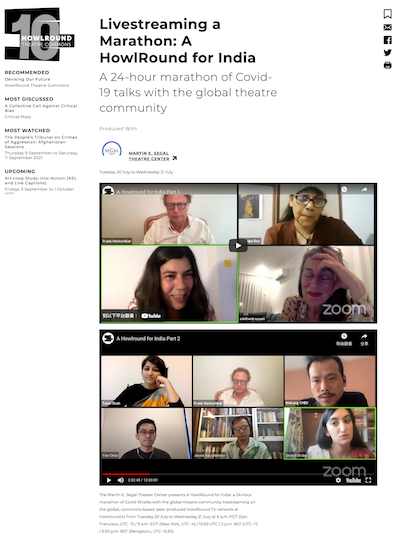
原本歌德學院國際共製平台要以十天在香港進行密集工作坊,因疫情演變成一年之中每一個月網路碰面一次,然後在最後有四天密集的線上活動(你能想像每天上線三小時以上的講座嗎?)。這其中包含一位主辦人提出的「walking thoughts」的想法,在不同城市的成員兩兩配成一組,設定一小時內以視訊通話的方式,「帶著對方」在你的城市遊走。透過走路移動,來啟動不同思考的可能,當然也是一種對於卡在電腦螢幕前的反動。本來覺得會多少有些尷尬無語的活動,因緣際會下我和韓國的媒體藝術家分在一組,從我們各自的家中走出,竟開始興味盎然地尋找起亞洲城市中的相同處。好比總有以變色LED燈照亮的橋,甚或是高樓上紅色霓虹燈的十字架。一小時竟然很快過去了。而連續四天的線上交流,也似乎讓這群根本沒實際見過面的創作者、製作人和機構代表,從開始時斷斷續續的問答,突然能在最後一天,真的開始在Gather Town上面天南地北的聊著。
透過一關關的試煉,我總算覺得有點經驗了,這時候要面對的是戴上VR頭戴顯示器、化身為一個虛擬分身,站上威尼斯影展的虛擬舞台分享我的VR360影片《霧中》。這還是讓常常與科技相處的我心驚驚。我早了幾天搞清楚怎麼以分身在VRChat軟體中移動、轉身、拍手(甚至翻跟斗)還有開關麥克風。也因著《霧中》受到虛擬平台對裸露的限制,而必須從原定的競賽片,妥協改為非競賽的特別選映,我特別以1.99美金去訂製了一個baby blue的露腰上衣配超短熱褲的虛擬分身,想以Queerness(酷兒性)攻佔虛擬平台。萬萬沒想到的是,本身有五六個分身的威尼斯影展VR單元共同策展人米歇爾.雷爾哈克(Michel Reilhac)看到我後馬上變身為一個漂浮著的、僅穿著一件白色CK內褲的裸男來力挺。大家見狀便紛紛複製了他的分身,於是我們照出了恐怕是史上最荒謬而超現實的紅毯照。


寫到這裡的我,已在9月24號早上。昨日,還是零人確診。
我突然覺得,其實我們真的還蠻agile(敏捷)的。因為我們是人,是那個劇場結合科技的創作中,最快能應變的有機體。我們找到辦法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容易接觸到彼此,我們找到方法自娛娛人,我們找到方法團結的站在一起(或說飄在一起)宣告藝術的表達自由不容侵犯。這是一場一路上總是一個人在家的網路壯遊,但卻和真實的壯遊一般,我們總會遇到同伴、嚮導,雖然不免迷路、雖然心中連滾帶爬,但因著這些旅程中意外獲致的驚喜,我發現自己,應該還能夠很敏捷的,再爬一陣子。
周東彥
狠劇場及狠主流多媒體(www.vmstudio.tw)藝術總監,創作以影像與劇場為核心。2020年於墨爾本Asia TOPA三年展首演台澳共製劇場作品《虛擬親密》。2021年以VR作品《霧中》入選威尼斯影展、日內瓦國際影展及蒙特婁奇幻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