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在思考疫情對於藝術創作者有什麼影響的時候,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這個世界五光十色的樣子。確實在疫情之前我很喜歡去各地拍照,並不是要去什麼特別的地方,只要是我沒有去過的,哪怕只是台北的某一個我沒有去過的捷運站,我都會像是去到一個新大陸一樣的興奮。我過去的創作常常都是從這些特殊、新奇的經驗當中發展的,譬如「台灣聖山」是跟風景攝影的工作相關,「台北民宿藏畫」是取材自我擔任民宿攝影師的經驗,「名人肖像」是從我拍攝藝文名人肖像的工作成果發展出來。
但是我接著想,這其實有點奇怪,因為我並不是那麼關心社會的創作者,至少相比於其他社會導向的藝術家,我沒有長期關注的社會議題,作品也不採取田調或是社會參與的方式。所以我對於疫情之前外在世界的眷戀是,我可以發現某種特殊的現象,但是這個現象並不是我真的想要探究的,而是這個現象可以讓我有一個奇特的機制,把不相干的東西結合在一起。譬如在「台北民宿藏畫」這系列作品當中,我並不是真的想要去談論台北的社會底層,也不是要處理弱影像或是藝術的複製性;而是有一個地方把這些元素以我從未想像過的方式結合在一起,我喜愛的是那個關係,而不是主題。如果要用一個說法去區分這種創作方式與社會參與的創作之不同,我想大概就是「以現實為形式去處理藝術」,跟「以藝術為形式去處理現實」的差異。

表面上來看,疫情對於我的影響會比起對於那些具體關心某些社會議題的創作者小得多。因為如前所述,我本來就沒有以一種研究的態度去處理我跟社會之間的關係,我也沒有進行過所謂的田調或是社會參與的方法,這樣的話,封不封城對於我有什麼影響?可是並不是這樣的。我覺得當我切斷了跟社會的連結,我更感受到一種創作意義上巨大的窒息。因為我想不出比社會更荒謬的東西。我待在家裡所設想的各種創作,幾乎都是很有意義的東西,譬如想要探究疫情期間藝術的現場性問題,我想要研究一種真正發揮線上展覽價值的形式,或是想要拍攝外送員送來的食物。我發覺一切都太理所當然了,太具有一種社會研究的價值。但是當我在社會之中,我反而可以發現許多沒有什麼社會研究價值的微小細節,那反而更讓我接近創作。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我覺得是因為「社會」或是「世界」其實根本不是一個東西,而是由各種不同的人、不同的社群所組成。當我們實際身處其中,我們並不是在一個世界裡,而是在一個充滿裂隙的荒原之中,從一個村莊走到另一個村莊,而發現這些村莊的差異,發現它們不同的習俗,讓我們有一種獵奇的快感。我們對於單一世界的想像於是被打破了。可是當我們人在家裡,我們反而會去認定這個社會是一個社會,有著既定的樣貌與連貫的邏輯。所以我們總是鼓勵藝術家走出去,這不僅僅對於攝影師成立,整個當代藝術圈也都鼓吹這樣的觀點:藝術家把社會當成一種異質、多元的存在,而藝術家的任務並不是去反映社會的真實,而是去展示社會的差異。這種說法有時候表現為現代主義跟後現代,有時候則是理念跟經驗,有時則是一元與多元,總之藝術家籠統地相信後者比前者好,而這一切的關鍵都跟走進社會有關係。事實上當後現代主義者批評現代主義的時候,他們正是從社會當中著手,控訴現代主義所宣稱的形式與價值不過是某種權力運作的結果。在這個信念之下,當代藝術成為了一種社會異質的競賽,越是能夠從一個現代性的、西方的、菁英的、一成不變的思維世界當中跳脫,越是能讓這些反思現代反思西方的學者/評審,覺得藝術能夠發現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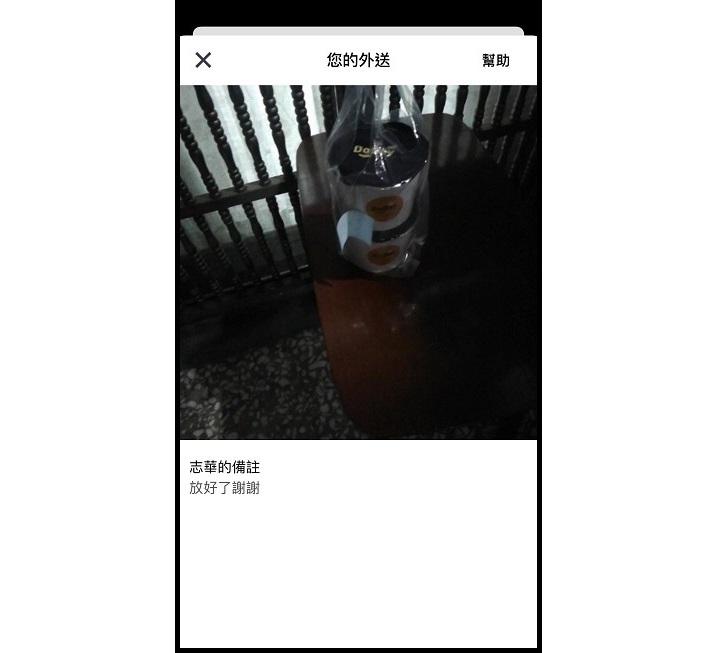

但是為什麼發現差異是好的?為什麼社會就可以提供我們這種差異性?我覺得這背後有一種階級的氣質。當我們處於一個比較低的位階時,我們並不會顧及他人的差異性,我們想的是融入大家,或者是往上一個階級攀爬。但是當我們可以用一種比較清明的觀點去審視各種不同的族群,我們事實上是從一個比較高的位階,對於社會採取了一種凝視。這種社會凝視有時表現為對於民藝的學習,有時表現為對於生態的責任,還有些時候是對於詢問藝術自身目的與法則的畏懼,但不論何者,我總覺得背後有一種藝術圈集體的負疚感:我們總覺得自己做的事情不實際,覺得自己脫離了世界,覺得自己有點高高在上。這並不是一個美學判斷,而是一個階級判斷。想想我們何時會覺得自己做的事情並不務實,然後覺得別人做的事情很務實。通常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我們做的事情真的很不務實,一種是我們面對比我們階級低的人,這時候我們就會特別容易覺得別人很實際,然後特別容易否定自己。後者實際不是真正的否定自己,也不是刻意擺出一種自省的姿態,而是自覺有一種義務要採取這樣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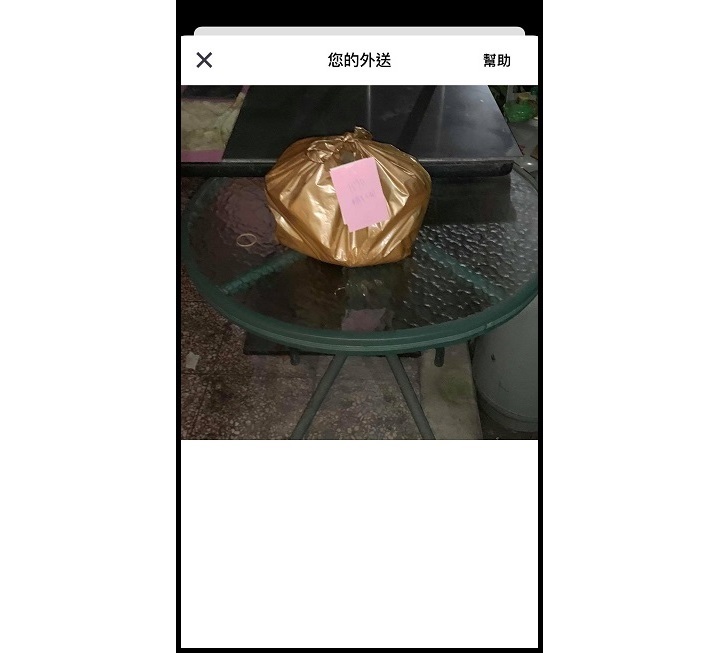

而疫情的爆發讓我們從這種悲憫社會的特權當中被降級了。我們不再是相對而言更具有空間移動與文化資本優勢的那一群人,我們跟所有人一樣困在屋子裡面,然後只有狹小的生活經驗。但是我們不放棄,仍然試圖從這個特殊的經驗當中想要提取一個藝術的觀點,站在社會之中也站在社會之上。或者是採取一種隱喻,但是施喻與被譬喻的都是我們自己。藝術家這時候有些挫折,可是轉念一想沒有什麼時刻比起現在我們更貼近於社會。試想社會之中大部分的人們並不知道社會整體是什麼樣子,也並不試圖透過他們的工作總結它。這種對於社會概念的缺乏,正是貼近社會的表現之一,可是以前我們並不珍視這樣的經驗,因為這與藝術家後設的看待社會這樣的觀點恰恰矛盾。如果說我在疫情期間對於藝術有什麼體會,那就是體會到沒有體會就是一種體會。這並不是一種平靜,而是一種挫折,我們終於得承認從自己的生活到社會不是依靠省思、批判與轉化可以變得更好。我們不是一個有自主性的個體,而是被病毒、公衛與社會結構綁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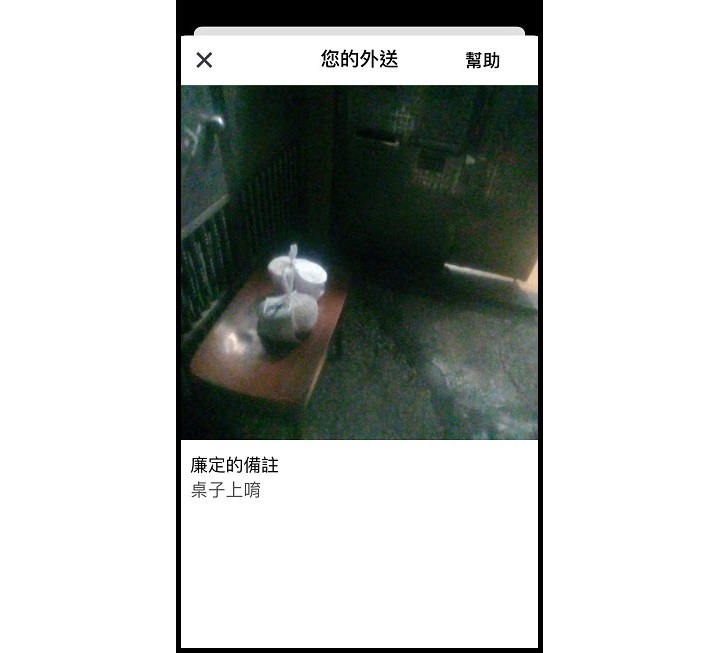

然後我想起我真正喜愛在馬路上亂走的原因,我明瞭那不是想要呈現社會的多元,也不是為了創作,而是我喜歡在目的地與目的地中間,我不屬於任何目的的狀態。這跟待在家裡完全不一樣。當我在家我確實是無所事事的耍廢,可是同時有千千萬萬的人跟我一樣的廢著。可是當我在街上,我看著上班族他們從公司出來吃飯,或是在公園的花圃前面抽一根菸,我與社會跟自己都產生了微微的疏離。我並不是想看到眼前的世界,也不是想閉上眼睛。我想要的是張著眼,但是沒有真正在看什麼東西,像是坐在計程車上,窗外所有的人不斷地過去,像是看電影,在劇情最緊湊的時候,我屏住了呼吸。我喜歡這些時刻,我覺得我是一個人。
汪正翔
1981年生,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後赴美攻讀藝術攝影。創作以觀念/行為攝影為主。目前看得見,會按快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