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若你從楚門的世界醒來
從1990年〈速度的故事〉到2020年《我們幹過的蠢事》,賀景濱與台灣文壇的十年一會早已被流傳到氾濫程度。回望傳奇的起源,〈速度的故事〉在解嚴初期上演了一場輕盈的逃亡秀,以哲學辯證劃開存在主義式的無解困境,黃錦樹引用李喬的評論,說小說家的作品能自足自在的飛翔,姿態吸引無數讀者作者昂首追尋;去年賀景濱交出第三本書,小說家的身影在作品中逐漸厚實,我們終於能在那些反覆出現的主題中,看到重新認識賀景濱的一條小路。
《我們幹過的蠢事》從尋找邏輯學教授開始,小說家主角對小說敘事的正當性產生質疑,渴望從困擾自己的循環論證中逃脫。回到短篇集《速度的故事》的「李伯夢三部曲」,李伯夢在逮捕事件後不斷逃離那份創傷;到了《去年在阿魯吧》,虛擬城市巴比倫的市民LMA試圖協助ROM逃往現實世界。在輕盈的背後,賀景濱也總是展現強大的禁錮,從中逃離就成為小說家推動故事的主要來源。
「莎士比亞說,漂泊者都是反叛者,他們不愛他們的出身地;奧爾嘉.朵卡萩的《雲遊者》講人為什麼要離開他的出生地;商禽的一生跟他的詩也一樣,都是在逃亡。」一口氣舉了三個例子之後,賀景濱說起自己最初意識到的禁錮。
「我二十幾歲時,台灣還在戒嚴,整個台灣對我來說是很可怕的,那種低氣壓是讓我……我已經不想活了那種感覺。」賀景濱苦笑,說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感受,但他當時連寫一個字都很痛苦,卻無法把這份痛苦如實寫出來。那時少年賀景濱在政大念中文系,同儕為他打開眼界,卻看見自己活在一個經過粉飾的社會。
「第一次接觸到二二八,那是整個震撼。我小時候甚至是想殺朱拔毛、反攻大陸的人,就這樣活了二十幾年,所有家裡、社會環境沒人跟你講這事,不敢提、提都不敢提。到威權開始鬆動,黨外雜誌興起,我們才知道什麼叫二二八。你整個人被欺騙了,活在一個楚門的世界裡。」
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賀景濱則說二二八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但他從大學以來的心路歷程不只如此。賀景濱描述當時層層疊加的苦悶,像是一名大霧中持續前行的登山者,手上緊握保證性命的登山斧,每一次敲下卻依然危疑,不清楚自己是在攀登、打轉,或是即將墜落,只能在力氣耗盡前苦苦地多踏出一步。
「那時的中文系困在樸學裡,大二文字、大三聲韻、大四訓詁,我很受不了那些東西。」賀景濱原本想念的是哲學,但不確定要從西哲或中哲入門,他高三時找國文老師討論,結果中文系就成了唯一的志願。入學兩年,賀景濱圈讀完幾部經典,提早完成研究所畢業的門檻,也發現這不是自己想做的事。
「到大三、大四,我覺得我可以寫點東西。坦白講我要開始創作是被二二八震撼到,但我一直寫不出來,我還沒那個能力處理那麼龐大的悲傷;那個東西還抓不住,好像遙不可及,只好從其他東西開始寫。」
望向太過遙遠的目標,賀景濱的起點之一是散文。《文心雕龍》一開頭就說「文固有體」,文章的內容其實會被體例限制住,他想反過來顛覆這個說法,於是擬仿各種制式文體寫戲謔的內容,陸續完成〈我的政見〉、〈如何改造不滿分子〉等散文,也揉雜圖像、符號和辯證等書面紀錄形式,寫下明指白色恐怖的短篇小說〈免疫的故事〉,為後來的「李伯夢三部曲」開了頭。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說集,賀景濱的計畫已經安排好,卻在寫作過程中逐漸陷入泥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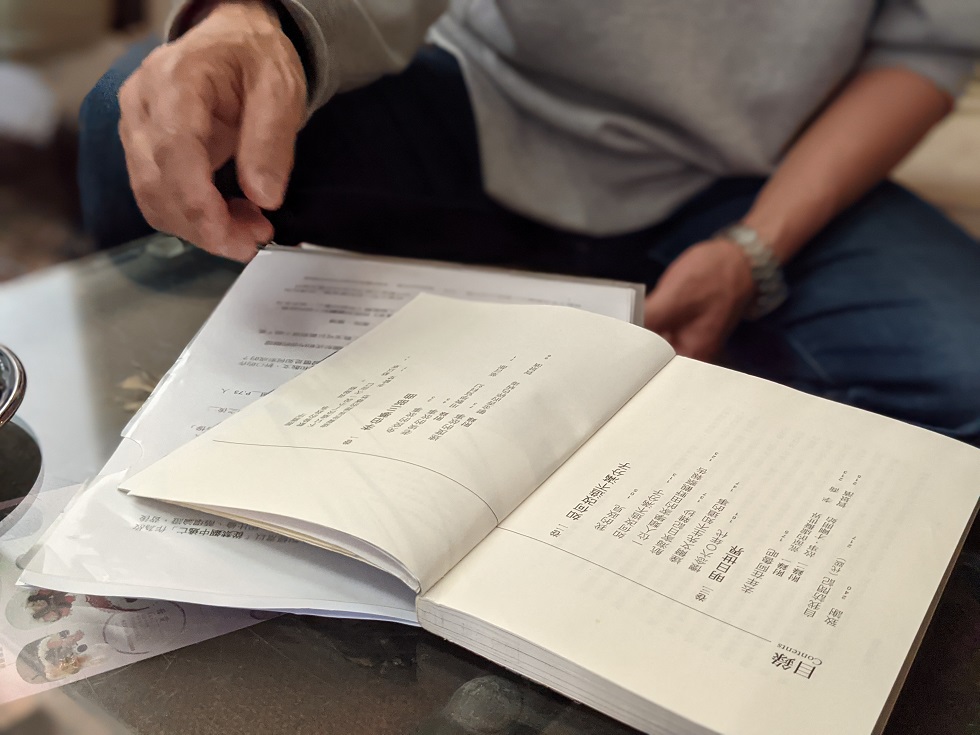
「大二的選修英文課,老師給我們讀D.H.勞倫斯的文章,談為什麼寫作,那給我很大的衝擊。中國文人寫文章可以得到功名,所以他不能去思考這個問題;當我看到這種文章,我會想,為什麼一個作家會去問這個問題?海明威接受《巴黎評論》訪談時答過這一題,大意是說虛構的意義是創造,它的背後有個東西是不能質疑的,不管是語言、文字或靈感,你要是質疑那個東西,寫作就會陷入虛無。」
得知二二八的衝擊太過強烈,揭開了世界的一層面紗之後,賀景濱無法相信文學對他毫無隱瞞,無法被寫作舒緩的創傷逐漸深入內在。威權社會的禁錮讓他寫得萬分痛苦,作品中慧黠的語句看似調侃威權政治,在當下時空也是為了迂迴閃避。散文寫了幾篇,賀景濱意識到這終究只是畫靶射箭的遊戲,反抗形式只會繼續被形式困住,傳奇的〈速度的故事〉完成後,他覺得自己再也玩不出新的內容,又找不到新的形式,就這樣停筆了十多年。
「那時候沒有憂鬱症這三個字,我現在回來想,那就是一個得憂鬱症的小孩。」回顧大學立志寫作以來的苦悶,賀景濱笑著這樣說。問他怎麼脫離那樣的狀態,賀景濱說他永遠無法回答自己這個問題,也許是大環境變了,更可能是他的身體也改變了。
「演化論有一個說法,人類文明的進步是因為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一定要離開他的家,因為他對現狀不滿,會想改變現狀,離開他的家庭、社會、國家,他們保護了你,也提供了一種禁錮。感受到禁錮之後離開,開始做某些事情,那就是和禁錮一體兩面的逃亡。」賀景濱1987年開始發表作品,到1991年暫時封筆,往後的十幾年裡,賀景濱逃亡的步調稍微緩了下來,心態逐漸遠離青春期的焦慮與憂鬱,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也開始改變,彷彿自我放逐的階段過去,賀景濱還是寫起了小說。
如果當年選擇的是孕育無數作家的外文系,是不是可以不用經歷這段空白?賀景濱只是拿出老話,說創作者永遠是孤獨的。「你沒有進入過那樣的狀態,你沒辦法寫作。」
懷疑論者面對政治與愛
2005年,賀景濱再度現身,以《去年在阿魯吧》的第一章獲林榮三文學獎,一直被擱置的作品也得以集結,半本散文和半本小說合為《速度的故事》出版。熬過了口腔癌的治療,《去年在阿魯吧》在2011年出版,透過虛擬現實的技術質疑世界是否真實存在。
「我們認知的世界,永遠處在你需要去審視和批判的狀態下。」賀景濱說,解嚴後的政治禁錮不再絕對,他卻開始感到另一種禁錮,可能來自文化、思想,甚至是基因這種天生要束縛自我的存在,這樣的慣性讓他在小說裡屢屢以懷疑論者自稱。得知虛擬現實這項技術是他寫出《去年在阿魯吧》的契機,撐起內容的則是他思考三十多年的種種問題。
寫完《去年在阿魯吧》,賀景濱發現自己討論了世界,卻還沒討論個人的主體性如何能夠存在。於是《我們幹過的蠢事》將個人意志分解為一條條資訊,拋出各種情境詢問資訊的根源,敘事者的語調少了輕佻和狂歡,變成了一名對自身處境焦慮不已、努力尋求小說敘事正當性的小說家,被夾在德國情報局與不受政府管制的暗網的對決之中,只能暈頭轉向的奔走。虛構與絕對、自由與管制,整部小說隱隱呈現小說家與過往威權對質的態勢。
「海明威說,文學要不朽就要避開政治,可是你會覺得喬治.歐威爾的小說很爛嗎?其實海明威說的是狹義的政治,〈我的政見〉寫到的就是,但那個已經過時了。我們講廣義的政治,講的是權力,只要有兩個人就能產生權力的關係,要談論自由就離不開權力。」

《我們幹過的蠢事》總共九個章節,故事中的小說家在第五章寫出了為虛構敘事取得正當性的小說論,在第七章找到了他的邏輯學教授,情報局與暗網的對決永無止境,小說卻在一位疑似來自暗網的「老闆」現身後戛然而止。不斷逃離管制的暗網竟也浮現體制的黑影,最後一章「我們老闆想見你一面」,以白色恐怖時期足以宣判死刑的一句話命名,彷彿嘲諷尋找小說敘事正當性的旅程:政治的敘事就是正當性,即使自稱懷疑論者的小說家,也無法在小說中提出質疑。
「那可能呈現了現實世界的某部分,但重點不在政治不政治;作為一名作家,你沒辦法忽視不義。小說敘事的正當性其實是,你要從世界裡面找到不義的來源。世界塑造了人,而小說呈現這個世界,描寫行為、事件之間的關係,看看它們之間的連結如何產生。只有找出那些蛛絲馬跡,你心中對不義的看法才會浮現。」
賀景濱說,不義的來源其實是資訊不對等,政府統治人民的基礎也來自資訊不對等。《我們幹過的蠢事》收在酒吧外將「老闆」捲入的爆炸,小說家手上的末日時鐘卻倒轉了四分鐘,過去輕盈的逃亡不再,彷彿暗示人類文明的存續的關鍵依舊是管理而非自由。但賀景濱說事實也未必如此,現實中的末日鐘在去年一月離午夜只剩一百秒,故事中的末日鐘也只是大數據計算後的結果,甚至可能根本和爆炸無關。是否相信鐘面顯示出的末日倒數,終究要看每個解讀的人相信什麼。
和剛開始寫作那幾年不同,指出現實之後,小說家展示的路不只是接受或反抗的雙向道。《我們幹過的蠢事》雖然有賀景濱一貫的幽默語調,態度卻比過往都更加尖銳,甚至到了嘲諷的程度。「生活在權力之下,有時候你不得不幽默,不然你遲早會自殺的。面對權力的壓迫,你要嘛死亡,要嘛幽默以對,像伽利略那樣。」賀景濱說,很多人容易把嚴肅和幽默對立起來,但大可不必。
「藝術永遠是娛樂,這是離不開的本質,把它當成嚴肅的東西只會限制自己,問題是我們對幽默的了解還不夠透徹。我覺得卡夫卡的小說就有喜劇的成分,有閱讀的趣味,但也還是很悲傷;嘲諷也是一樣,不能只是展示讀者預期之外的某些東西,讓人笑完之後,可能還得讓人哭出來。文學談論的總是宿命跟自由意志的拉扯,而幽默比嚴肅能讓人看到更多面向,有時會是更加深入的、在宿命之外的事物。」賀景濱說,自己曾在德國住了一個月,覺得這個國家實在太嚴肅了,相對來說台灣還是好笑一點。但人類會為了什麼發笑?笑又有哪些意義?一談到這些問題人們就嚴肅了起來。泰瑞.伊格頓在《論幽默》分析得不錯,可惜他的態度太嚴肅了,也許伍迪.艾倫會做得更好一點。

小說討論的主體性問題到這裡變得越來越清晰:如果自我是演算法推算出來的虛像,那麼個人的意志如何存在?如果自我並非來自演算法,那小說家如何有權在現實中虛構?為了回應這個問題,勢必得提出一些科學和小說都無法觸及的事物。在賀景濱的作品中,和「不可質疑」的政治對立的,那一貫「無須質疑」的未知,指的往往是愛。〈速度的故事〉中李伯夢和唐娜無需解釋的愛、《去年在阿魯吧》愛上死去女殺手記憶體的LMA,即使《我們幹過的蠢事》出現了「完美情人」app,使用者可以捕捉資訊構築理想愛情對象,小說家依然堅持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完美符合演算的結果,而是情不自禁。
「文學有兩大主題永遠逃不掉,就是愛和死亡,這兩個東西拿開,可能就沒有文學了。愛是讓人類聚合在一起,變成龐大社會的基礎,你不可能把愛拋開而成為一個社會、不可能離開愛這個主題。」但賀景濱談的不是浪漫主義時代的愛,而是與科學共同拆解愛的賽跑。過去人們認為心靈、意識、思想專屬於人文領域,但科學已經把這些活動拆解成激素和電流,交友軟體用演算法揣摩愛的輪廓,到了一百年後,或許我們真的會看到能愛的機器人,但在那之前呢?
「人文領域如果不碰愛這個東西,等於是你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我們現在談愛不像以前談愛就是這麼理所當然、理直氣壯,我們要自己找到這個時代談愛、談死亡的基礎在哪裡,才有辦法產生你這個時代的愛跟死亡。我在小說裡說愛就是情不自禁,那你要怎麼設計出會失控的機器?」
小說中的修車工馬肯森說,愛一樣東西遲早會把它分解,才能搞清楚自己愛的是什麼。不斷將事物分解為更小的存在,那就是西方文明能發展到這地步的基本動力,而即使如此,馬肯森用精湛工藝製造的求愛玫瑰,也在真正的愛出現時被摔成粉碎。賀景濱說,自己還找不到足以質疑、消解愛的立足點,以後能不能找到也不曉得,只能讓它繼續是一種無需質疑的存在。

面對我經歷的那些時代……
《我們幹過的蠢事》延續了《去年在阿魯吧》的長篇敘事模式,也加入《速度的故事》揉雜各種文體的特徵,以不同角度的敘事取徑,試圖接近問題的核心。賀景濱說,他成長的時代是整體化的時代,如今時代走向碎片化,同輩人往往感到憂心害怕,他反而迎頭走在最前端。
「以前我們很自然把世界視為整體,可是到了碎片化的時代,我們應該回頭考慮這種想法是不是有缺陷的。唐娜.哈洛威講過,碎片化不代表對解放的徹底絕望,而是要有別於整體化革命的語言。總體敘事的時代是像托爾斯泰或托爾金那樣,可是你看到碎片化,你會想到用新的形式去敘事。」
傑出的藝術通常也是在形式上有所突破的作品,賀景濱說,他這一代是很特殊的一代,對於自己的時代,他成長、面對的事物,他還欠自己一部小說。
「我從農業時代走到工業時代、從工業時代走到資訊時代,一個人匯集了三個時代,人類文明三個時代我都經歷過了,雖然前後可能都是沾個醬油,但我的時代就是那麼特別,我們一直被逼著進入另一個時代、不想進入都沒辦法。我要抓住的不是黃金年代的回憶、不是光寫事件或歷史,重要的是,我碰到了什麼東西,我要怎麼面對那個東西……」賀景濱說得激動起來,喝了一口咖啡,有點倉促地總結,「反正我的自我認同永遠是一個問題。台灣人永遠是一個問題。」
討論過世界、討論過個人,賀景濱說那些小說都是為了遙遠的這一部小說,討論他的自我的小說。他說他的小學校訓只有四個字,「來學做人」。「我們是不是該先學會做人,才有辦法談怎麼做個台灣人?」總是展現輕盈逃亡的小說家,原來一直在尋找降落台灣土地、回歸自身軀殼的方法。
「那是我一開始就想寫、也是最想寫的一本小說,我不曉得我有沒有能力處理,但那是一定要解決的東西。總是要寫的吧。」
賀景濱作品
《我們幹過的蠢事》,春山出版,2020
《去年在阿魯吧》,寶瓶文化,2011
《速度的故事》,木馬文化,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