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是鏡之妙妙乎能易物象也何謂易象蓋凡物之有形者必發越本象於空明中以射人目
——〈原繇〉,出自湯若望著,《遠鏡說》。
「我特別喜歡那種假的文化。」
梓安聊著阿塔納修斯.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1667)裡面登場的Pussa(菩薩)畫像,又聊著英國小說家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筆下誕生的人物傅滿洲(Fu Manchu)。當他愉快地在他腦中的映像庫裡調閱著各種關於「虛假」的圖像時,我腦海中也浮現了歐弗特.達波(Olfert Dapper)在其17世紀的著作中出現的媽祖(Matzou)像,以及梓安於2017的作品《少女的祈禱》中,兩位拿著西洋劍、穿著日本水手服的少女在墨爾本天后宮的前面擊劍的樣子。


之後我們一同往前追溯了上世紀90年代的動畫《少女革命》(少女革命ウテナ,1997)中,於螺旋樓梯銜接的高台上進行的西洋劍格鬥畫面。其中讓人印象深刻的,便是那位著男裝上學的女主角歐蒂娜。接著,我們又往前踏入80年代前後的動畫《凡爾賽玫瑰》(ベルサイユのばら,1979 - 1980)。「對我來說,它其實是一部穿越劇,」梓安說道,「你看在那個一切真實的歷史人物都那麼考究的作品裡面,放了一個女扮男裝的虛構角色。作者讓這個角色在歷史裡面活動,卻充滿了說服力。而裡面扮男裝的女子奧斯卡,簡直是現代的人物穿越到了古代。」
這種穿越像是一個遠行的旅人,如同馬可波羅抵達東方,通過他的眼與耳,在親歷的萬象當中雖盡力捕捉,而無可避免記述的內容真假摻合。梓安很快地提及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在電影《龐克狂歡城》(Jubilee,1978)當中,也安排了穿越。電影中,莎士比亞《暴風雨》裡的精靈愛麗兒(Ariel),那位曾經吟詠著「他的骨已成珊瑚,那些珍珠曾是他雙目」的愛麗兒1,領著16世紀後葉的伊莉莎白一世穿越至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四顧並觀察著虛無主義如何在城市當中逡巡。而在梓安的《此岸:一個家族故事》(2020,以下簡稱《此岸》)當中,我們也看到一個穿越者:飛行的荷蘭人。這位飛行的荷蘭人或是徒步,或是乘船,在時空當中遊蕩。他的穿越本身,被覆蓋著相同妝容與穿扮的相異人體所紀錄,這位虛構角色的眼耳口鼻,圍繞在一個家族的遷徙與飄移周圍,猶如泡沫表面高速旋轉的薄膜,包裹在透明的真實空氣之外。

這層虛構的薄膜,是如何開始在梓安的創作當中浮現的呢?梓安在大學時代參加社團活動時,很快發現自己在電影種類上的偏好。「如果把電影的脈絡分為靠梅里愛的《月球旅行記》那邊,和靠盧米埃兄弟的《火車進站》這邊兩種的話,我一開始無疑是靠向梅里愛那邊的。」那時讀著性別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他,對於變裝皇后(Drag queen)文化有高度的興趣,並且在他第一部作品《明星花露水》(2005)當中,也初次呈現出他嘗試以影像的手段表達他的觀察與想像。裡面變裝的男子經歷了一段羅曼史後,最終在鏡子前面將自己的妝容、假髮與穿扮一一卸除,回到了現實社會,卻在結束的剎那遇到了非現實的計程車司機。梓安笑著說自己那時什麼都還不懂,對於拍片所需的專業技術也完全陌生,但此時的他卻已經展現出:預備從虛構、虛假、虛偽的境域出發,一邊逼近「可能不存在的真實」,一邊又與這真實保持著容髮的距離。

「我不認為我自己的東西會不實驗,」梓安一邊傳出靦腆的笑聲,一邊卻又果斷地說,「因為我人是這樣,我就是這樣看東西,所以拍出來就是這樣。」他於2009赴紐約新學院大學(The New School)媒體研究所就讀時修了錄像藝術家保羅.萊恩(Paul Ryan)開的課,老師在課堂上要求他們:每天要拍三分鐘不間斷的東西,「建立身體跟相機的觀看關係」。在數門相關的課堂當中,梓安讓攝影機的鏡頭慢慢成為他自身的眼睛。此後至2013中間創作的發展,我們益發可以觀察到:在運用這顆「眼睛」捕捉他自身的肉眼所見景象的同時,也顯影出包裹在事物之外的朦朧的薄膜。「我發現若要選擇很真實的去演一個東西,或很造作的去演一個東西,我會選離真實遠一點的那邊。」在他的作品《We Can't Grow Up Together》(2010-2013)當中,雖然探討的是成長此一帶有紀實氣味的主題,但他卻選擇在真實的場景中,運用假的童年回憶,變裝與蒙太奇手法,讓外部的真實世界,與一個角色內心的情緒轉折,隔著一層薄膜——或我們說鏡子——彼此對視。而在《日常日長》(Quousque eadem? (or a self-portrait),2012)當中,伴隨著虛假的影像日記出現的,是重複映照著此虛假肖像之群鏡形成的殼膜(與江戶川亂步筆下的「球形鏡」遙相呼應,詳後文)。


在紐約的期間,他一邊嘗試使用數位攝影器材進行創作,一邊卻也更加好奇膠卷的作用方式。梓安表示,美國紐約某種程度上繼承著一個實驗電影脈絡的正統。從20世紀後葉發展起來的,諸多利用膠卷本身的特色所進行的實驗與創作手法,五花八門地羅列在梓安面前。他很謙虛地表示自己並沒有受過很嚴謹的訓練,不過在數年下來的練習當中,他「發現膠卷雖然充滿操作技術,充滿很多限制,但若手法越來越熟練,就能越來越個人化」。他不僅學習膠卷的沖洗與上色,同時也更加深入攝影器材本身的特徵。「當我在運用不同種類的膠卷進行拍攝時,我會想要呈現出不同機械的特性。」例如他在《此岸》中使用的super 8 mm膠卷攝影機重量較輕,適於手持,因此他會傾向於讓這種攝影機的拍攝更接近「隨興所至的觀看」,而營造出令人暈眩的視線。相對的,若使用 16 mm膠卷的攝影機拍攝時,由於機器較大台,他多半會選擇使用腳架,彷彿是在虛空中對被攝物的一道凝視。
「而且用膠卷拍攝的話,」梓安接著說道,「為了節省成本,一定是累積一定的量才會進行沖洗。所以通常是隔三個月以上,才會看到膠卷本身的效果。一看到,就發現和自己的肉眼所看的東西差很多。可是那個感覺就是,和自己看到的東西很不一樣,所以很奇異;同時又和自己看到的東西很一樣,所以很真實。」這時我們很快就能注意到,膠卷此一媒介,如何在梓安創作中成為了一個狹窄的夾層,容許虛與實在夾層兩側彼此蠢動著注視。這時,我們需要將視線移到梓安以super 8 mm拍攝再進行數位後製的《伊人》(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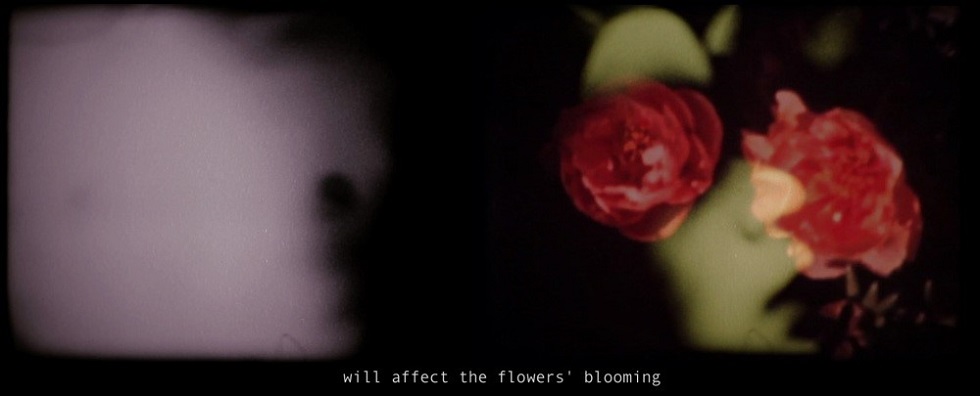

作為雙屏影像並置的《伊人》,在梓安眼中就像是音樂中的對位(counterpoint),又像是兩道訊息的對話。「它同時是一封情書,又像一紙恐怖勒索信。」虛與實、數位與類比、機械性與生物性等成對的概念,在這部作品當中以極高的速度切換著彼此對看的位置,有時各自獨立,有時又在剎那間形成一張和諧的構圖——甚至是一張臉。在此作品當中,我們不難看見曾經在賈曼的《鏡子的藝術》(The Art of Mirrors,1973)以及《日影之下》(In the Shadow of the Sun,1974)等以super 8 mm拍攝成的作品的手法與美學元素。「賈曼其實就像是用super 8(mm 膠卷)當作素描簿,拍攝非常多素材,並且在那段時間的各種作品中重複應用。」梓安從賈曼的作品當中獲得了一些啟發,在《伊人》的第二次拍攝工作中,他先使用一秒九格的方式拍攝,之後再進行播放速度的調整與數位上色,以符合自己心中理想的預期效果。
2016年開始,梓安說明他開始以日記般的方式——使我們想起瓊納斯.米開斯(Jonas Mekas)的日記電影——斷斷續續地創作《此岸》。這部實驗紀錄片,一方面彷彿繼承著他在《Proxy of Heaven》(2015)當中對於死後與生前的探問,一方面他也更加熟練於以虛構、虛假去逼近、反映、包圍所謂「真實」的敘事手法。我們看見橫貫在《明星花露水》、《We Can't Grow Up Together》、《日常日長》、《少女的祈禱》與《此岸》中的彩色泡沫與各種鏡子。而其中,鏡子這種塗敷有金屬膜層,而能夠以虛照實的物件,特別受到梓安的注意。以虛假的日記構成的《日常日長》當中,伴隨著夾在鏡子與鏡頭之間的多重肖像一同出現的,是這樣一段旁白:「在江戶川亂步的小說《鏡地獄》中,主角進入了球狀的鏡子,沒有人知道他在裡面看到了什麼。」而那球狀鏡的鏡子部分,到了《此岸》裡面變成了手鏡,總是把真實照成一圈圈模糊的光暈;球狀鏡的球的部分,則成了漂浮的泡沫,儼然為遊蕩的穿越者——飛行荷蘭人的隱喻。鏡子的金屬膜與泡沫的液體膜,猶如梓安藉由乘載影像的膠卷,從虛構凝視真實的夾層。


江戶川亂步與吳梓安的聯繫,不只是小說本身。學生時代的梓安相當喜歡一個樂團:「人間椅子」,團名正來自江戶川亂步。「這個團的歌曲,經常把大正時期或昭和時期的元素拿來編寫成新的東西,我很喜歡那種虛構的元素。」梓安進一步說道,「他們有一首曲子叫做〈此岸御詠歌〉,有一種模仿佛經唱誦的感覺。這部紀錄片的片名,就是從這首歌出來的。」這首歌的歌詞:「究竟這裡是哪呢?是各處,也不是各處。既是這裡,也是那裡」,為《此岸》揭露一個註解般的提問:一個家族在歷史的推移下各奔東西,在影像所記錄的時空中,抵達了他們所在的位置,但這裡是哪裡?這裡是歸宿嗎?梓安一邊尋找可能的答案,一邊意外發現:隨著自己的拍攝工作進行,也陸續在家中挖出了一些照片、畫作與影像紀錄。這些影像有些是祖母參加的畫會聚會時,攝影師拍攝所留下的影像;有些則是以前的長輩使用家用設備所拍攝下來的錄影帶。「家族留下的這些東西,好像冥冥中在協助我拍攝。」梓安還說,他的家族中有不少人,擁有把事情說得繪聲繪影的天賦。而這些經由訪問而被勾出的講述,以及從倉庫中重見天日的影像與照片,像是亙古留下的群鏡,既模糊又斷續地映照出梓安所從屬的家族譜系之昔日面貌。「歷史很有趣,但拼不出來耶,每個人記得的都不一樣」,《此岸》中的這段對話,凸顯出真實本身的不確定性。之後,梓安更將穿插著這些昔日影像的影像放映給家人看,且再次把家人觀看的情景拍攝成影像。家人、家族所在之處,恰位於布面的影像之鏡與鏡頭之鏡間的夾層。到此,梓安已堆疊出好幾重虛實的夾層。每一夾層本身都顯露出:一側是多年下來益發洗練的膠卷——視網膜所捕捉的幻影,一側是轉瞬榮枯的浮世在每個剎那的群象。在那夾層中,梓安睜開了眼睛。

吳梓安2020新作《此岸:一個家族故事》預告片
(影像來源/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註1|“Of his bones are coral made: Those are pearls that were his eyes.” Quoted from Shakespeare, William, and John Dover Wilson. The Tempest / Edited by John Dover Wil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