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在我們眼前,人群如游魚穿梭,詩人說他昨天才到這來溜冰。原來咖啡館前這片印有可愛海洋生物的牆面是屬於溜冰場的,偷窺場內流動的大人小孩,他們也偷窺著我們,誰在裡面、誰在外面,已是不得而知了。

詩人曾貴麟來自宜蘭,於東華大學華文所畢業,2019年5月出版的詩集《人間動物園》是一本關於「展示」的詩集。詩集名為「人間動物園」,與世界博覽會曾經設有的「人類動物園」(Human Zoo)是否有關呢?
「『Human Zoo』台灣翻譯多以『人類動物園』居多,為了有所區別我選擇了『人間動物園』。從麥第奇(Medici)家族開始,將非裔人或原住民抓進莊園中,區分種族、產地、習性,彷彿是抓到長頸鹿或大象,這是帝國主義的主宰暴虐。日治時期也有日本軍展示原住民的案例。」「就像寶可夢圖鑑一樣分類。」曾貴麟這麼比喻。
雖然試圖與「人類動物園」區別,仍有某種共通性。曾貴麟這麼說道:「但我認為詩集何嘗不是這樣,將人間的情慾或際遇與現象節錄下來,也是一種展示。還有論述者在場的位置,不過我只用〈象族〉來延展政治性。」「我們以為我們正在觀看一個正在展示的東西,其實那個東西也在凝視著我們;大家都在籠子裡頭,只是看的方向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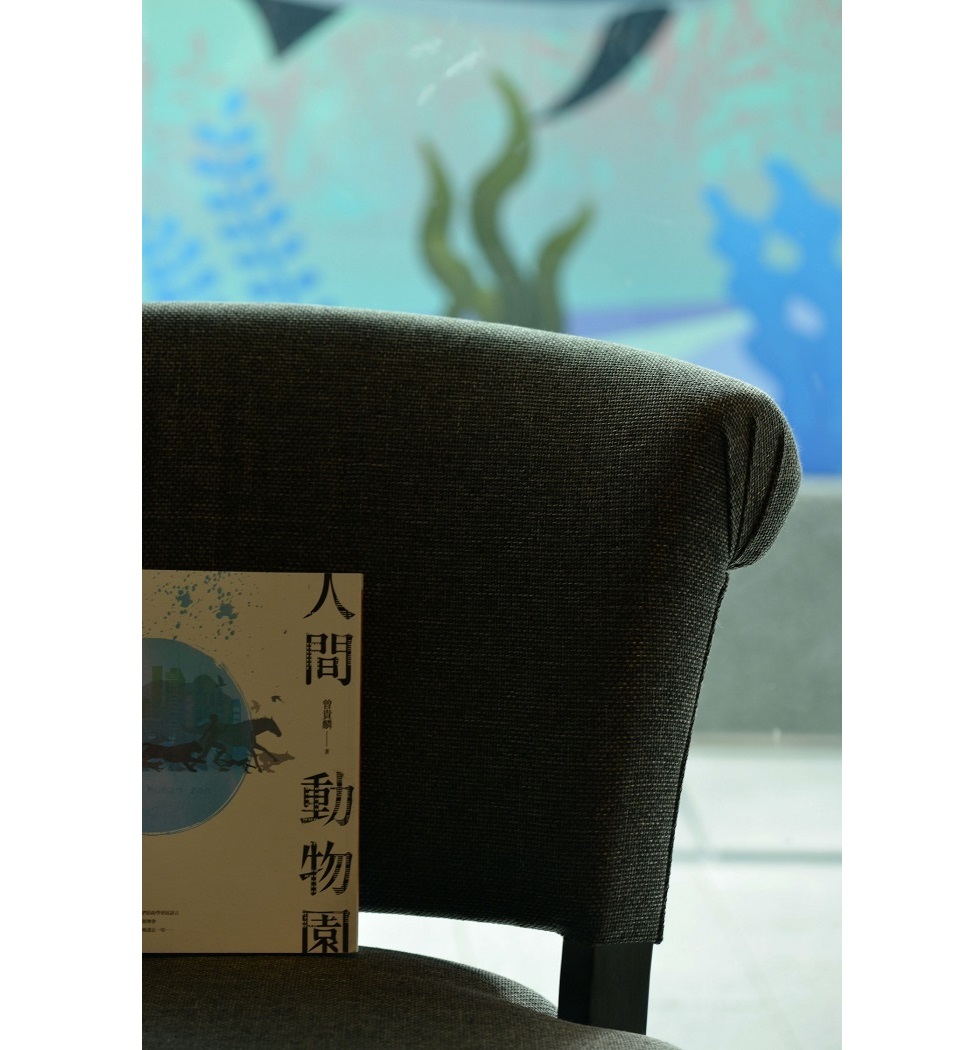
詩人是巨象的發現者
《人間動物園》分為〈象族〉、〈貓族〉、〈蟻族〉、〈水族〉,以及〈百葉窗:管理員寂寞的柵欄〉五輯。象即文明,貓族為細膩變幻的愛情,蟻族述說鄉愁,水族代表的則是深深的孤寂。百葉窗則比喻詩人與讀者親密又疏離、互相流動的關係。
詩與憂慮都是陸生 / 藏進象皮 / 眾人張開雙眼如槍管 /視線觸碰牠的巨腿、象牙 / 與生鏽的膚質 / 象的膝蓋──最初的壁畫 / 收錄剛剛產下,首次睜眼的字
——節錄自曾貴麟〈象說:受困於裝幀的獸〉
對曾貴麟來說,文明宛如一頭巨象。「『象說』在《說文解字》中是『比喻說法』,是一個轉化的過程,就是語言學當中『什麼東西轉化成什麼東西』,我覺得詩人就是在做這樣精緻的工程。」「每個人都在瞎子摸象,我們可能只發現了象的膝蓋、指甲,只能發現象的微小細節。」詩人是巨象的發現者,也是動物園的管理員。「從象的形,去發現它的義,象的形可能就消失了,詩人就是這樣在追逐形與義之間。」
不願被安置的靈魂
我的愛人自我體內分裂 / 如貓萬花筒般的眼 / 共用一具肉身,不同名字 / 縮起聲音,不斷互道:「晚安,晚安」
——節錄自曾貴麟〈貓性動物〉
貓派的曾貴麟曾當過多次貓中途,他認為這是他與貓最好的距離。「我喜歡這種關係。我陪伴牠等待最終的主人,然後送別。」
有一次他在宜蘭開車,一隻貓在眼前被車撞了,不顧被驚恐的貓抓傷,他趕緊送牠去醫院。沒想到醫院卻說需要先確認曾貴麟要認養這隻貓才能醫牠,要先簽名。「我看著那隻貓,我也不知道牠有沒有要給我養,但我還是簽了。」簽了之後他覺得對牠有種責任,在幾番搏鬥後,充滿野性的貓仍不肯乖乖吃他替牠準備好的食物。
「牠就是一個不願被我安置的靈魂,我發現牠快在我手上死掉了,終於把牠放到宜蘭的田邊,然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牠了。我那時才覺得我們和醫生簽的約、什麼動物的倫理,在這隻我還來不及命名的貓上面,一點作用都沒有。」

而最近收留的貓則命名為「躲躲」,曾經受過傷,是大小眼。「剛養牠時真的都看不到牠,各種躲,躲在窗簾或床底下,用貓的變聲器才叫得出來,而且也只有第一次有用。後來我忍不住懷疑,我到底有沒有養貓?只有飼料一直變少,好像在養一個無形之物。但後來牠變胖了,躲在窗簾後會看得到,才終於找得到牠。最後是我弟接去養了。」豢養每一隻貓的過程帶給曾貴麟不同的經驗,一如每段情感關係的相異。
依照個性和行為模式來說,摩羯座的曾貴麟則自認自己像象,「慢,也不擅長交際吧。」若是可以自由選擇,他則嚮往成為鯨魚:「鯨魚都有自己的房間,在海壓下如一個真空的房間,我想知道那個空間到底是什麼樣的?有沒有浮游生物經過?有波瀾在那個地方嗎?」曾貴麟不害怕孤獨,不怕只能依賴52赫茲與可能的另一隻鯨魚交流;詩人寫詩而有讀者偶然讀到產生共感,大概也是這樣的感覺吧。
跨域與變形
獸是不安定的,曾貴麟本人雖然不擅與讀者直接交流,也沒有經營社群專頁,卻運用許多跨域作品來打破與讀者互動的邊界。2015年他曾策展攝影散文展「25時區」,2016年在東華大學角落藝術節中於電梯展出〈訊號微弱〉一詩,並拍攝〈象說〉、〈愛的變形記〉等多部影像詩。

他的創作受到大量前衛藝術影響,他欣賞寺山修司,也寫詩向他致敬,看過他全部的實驗短片。長片則喜愛《拋掉書本上街去》、《死者田園祭》。「寺山修司在拍實驗短片時,也不會考慮說我是在拍『影像詩』,還是『詩意的影像』。」「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影像詩,鴻鴻做過,拍火車上的鏡頭;葉覓覓也做過,她近期的《四十四隻石獅子》已經是電影了。」另外他也很喜歡山村浩二早期的動畫,沒有劇情、很符號的,也令他非常著迷。
他近期也很欣賞侯俊明的作品,「他的訪問有點像行為藝術,訪問人怎麼看待自己的身體,文學性很高,他的圖像和神祇和傳統文化相關,跨了很多東西,比較直接的就是三個議題:政治、身體、同志。」他也不排斥寫劇情片的劇本,近期也參與了一個微電影的腳本,往各方面發展。
「鄉愁像是剛從日常生活出走的外遇」1
曾貴麟坦言,開始上班之後,自己也如一隻被困的獸。
「來台北上班之後,更有一種感覺:我雖然寫獸,但我自己也在裡面。在台北車廂的移動可能更有一種被箝制住的感覺,自由時間也少很多。」他還記得第一次從雪隧出來,見到陽光的時刻;遷移帶給詩人靈感,也帶給他再日常不過的疲憊。「以前都會覺得要時常遷移,現在可能沒那麼浪漫了。」
雖然受制於日常,詩人細膩敏銳的眼光仍日日在累積。他目前正籌劃散文集《私事》,創作時間是從大學末到研究所,是以「時間」出發。「這一篇我寫凌晨一點的台北,另一篇寫凌晨三點的台北,有點受到行為藝術家謝德慶的影響,我把打卡用寫作來實踐,變成一種『打卡寫作』。」
詩人自由穿梭於各種藝術當中,在他管理的這座人間動物園,我們看到各種扮演與展示,如一場假面舞會——或隱約或大方地秀出變幻無常的豐富情感,以及渴望解放的各種異色風景。

註1|引自曾貴麟〈家書——給年輕、初生,誰也回不去的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