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談起林蔚昀,腦中便直覺浮現波蘭這個有著沉重歷史的中歐國家,她翻譯布魯諾.舒茲、維斯拉瓦.辛波絲卡、安傑.薩普科夫斯基,將波蘭文學的瑰麗奇幻、暗傷沉痛、幽默自嘲都帶入台灣。多年來以語文翻譯與文學長才致力於台波文化交流,2016年出版首本個人散文集《我媽媽的寄生蟲》,這一回,她不再說別人的故事,以蟲為引,重新觀看與母親間的摩擦與親密,化身各種寄生蟲,用一個又一個蟲形的故事交代自己的生長軌跡,娓娓道出生命中的晦暗與光明。

《我媽媽的寄生蟲》記錄下林蔚昀自小到為人母親的身心蛻變,毫不掩飾地揭開滿佈傷痕的過往。青春期開始自殘,外在的印記時時刻刻提醒著所經歷過的人生,一道道如蛆般的蟹足腫恆久寄生。為了忘卻精神上的痛苦,忍受身體之痛以短暫移轉注意力,不惜自傷,更傷人。感受不到的所需的愛,孤獨與憤怒伴隨恐懼演變為暴力的肢體衝突,心理的破碎糾纏著對愛的渴望,她慣於破壞母親喜愛的一切事物,尤其是自己。「媽媽應該是很喜歡跟我在一起的吧?」母親對自己的情感一直像道難解的謎,直到自己有了兒子,才體會到父母在面對子女時產生的複雜情緒。
父母親皆為留美博士,家族中更有著數不清的老師、教授、校長……,存在血液中的「學術基因」,使得進入學術圈成為理所當然的世代傳承,林蔚昀的父母卻反其道而行,從不鼓勵她追求成就,只要她快樂就好,然而快樂的樣貌又是如何呢?學校課業、個人創作或者事業上的傑出表現都得不到父母親明確的讚美,要獲得認可是多麽困難的事情。日復一日摸索著,卻說不清它的輪廓是逐漸清晰還是愈加模糊。
如同一般家庭中兄弟姊妹們的暗地較勁,母親望向寄生蟲時從眼底流露的光芒與止不住的讚美也讓她感到吃味與不受重,擁有這一群數目未知的「隱形手足」,總感覺自己需要用力地爭寵,才能獲得所需的關注。成功說服母親移除體內群蟲,彷彿打贏一場勝仗般的喜悅,像個撒嬌、任性的小女孩,渴望獨佔母親,即便要以犧牲母親的學術夢想作為交換。寄生蟲既像是瓜分母愛的敵人,又像是自己的鏡中倒影。多次因母親的寄生蟲與先生爭執,林蔚昀於是開始思考,「我真的可以接受媽媽的蟲嗎?我對寄生蟲真的沒有看法嗎?是真的沒有看法,還是不敢有看法?」依附宿主的蟲之於依附父母的自己,倘若這樣的存在應當被質疑,那麼自己所有的情感、金錢需求,是否也應當一一抹除?母親的權威不僅僅來自於她母親的身份,專業領域的成就更成為兩人之間溝通的高牆,「她說的話對我來說就是權威啊,不只是因為她是我媽媽,還是因為她是個學者專家…,我好像很難去質疑媽媽說的話。」
獨立到底是什麼?
十七歲時的一個跳躍,從台灣跨到了英國。對電影「猜火車」的著迷,和著一些倔強,她選擇了以父母不熟悉的英國作為下一個落腳處。想像中獨當一面的自己,背離舒適溫暖的防護網,頭也不回地離開恆溫的玻璃罩,狠狠地朝遠方冰涼駛去。一心想著獨立卻仍缺乏足夠決心與勇氣,只得瑟縮於角落,好似「一隻大型跳蚤躲在地板空隙,忍受無盡的飢餓與苦楚」。英國求學的日子,林蔚昀過得相當孤僻,在感情生活裡更是極力壓抑著對關愛與依賴的渴望。厭惡水蛭那明目張膽、毫不在乎地用頭部吸盤汲取鮮血以獲得滿足的行爲,自己卻也依靠與人的親密感維生,如一隻愛情水蛭,蟄伏於潮濕的沼澤、草地和淡水,輾轉依附於一個又一個被麻醉的宿主,害怕被察覺,同時也無法停止索求。
移居波蘭以後,她決定一改封閉的作風,開始與人多方互動:受頹廢藝術家的危險氣質所吸引,學著跟波蘭式的「激烈對話」共處,處理生活中林林總總的狗屁倒灶,她彷彿不再是過去那個循規蹈矩以尋求團體歸屬感的小女孩。一連串未曾想過的「冒險犯難」,說是失控,其實也是勇敢。
兒子出生數月後曾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這三天的經驗成為一切混亂的重要轉捩點。因情緒不穩被綑綁於床的年輕女孩、四處徘徊、尋找兒女的失智老太太、手拿緊身衣恐嚇病患的彪形男護士、時刻受監視、毫無隱私的生活空間…,一旦真的進到這裡頭來,在僵固的醫療體系與思覺失調的迷霧當中,還找得到出口,還出得去嗎?精神病院中的所見所聞深刻得讓她清楚地感覺到,失去自由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於是告訴自己:「我一定要好起來。」
談起獨立的話題,林蔚昀很有心得,以前的她雖然獨立,卻像是迫不得已,硬著頭皮將自己推往一團混亂的世界,那樣子的獨當一面可能一碰便碎,更多的其實是孤獨。「以前強迫自己要獨立,後來會發現自己有的不是獨立,而是讓自己很無力,現在才去發現什麼是屬於我的獨立…我覺得自己知道自己的責任在哪裡,然後同時能夠對別人提出要求,並且能和別人互助合作,這才是真正的獨立,不然只是在孤立。」長久以來在極端依賴人與極端照顧人之間擺盪著,逐漸地摸索到之中的平衡點,學會接受幫助、學會呼救。過去總是害怕「打破平衡」會使自己成為一個不屬於任何地方的人,如今越來越能夠勇於表達自己真實的需求,她不再逼著自己展現堅強,逐漸知曉該如何讓他人照顧自己的脆弱,並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終於步往真正的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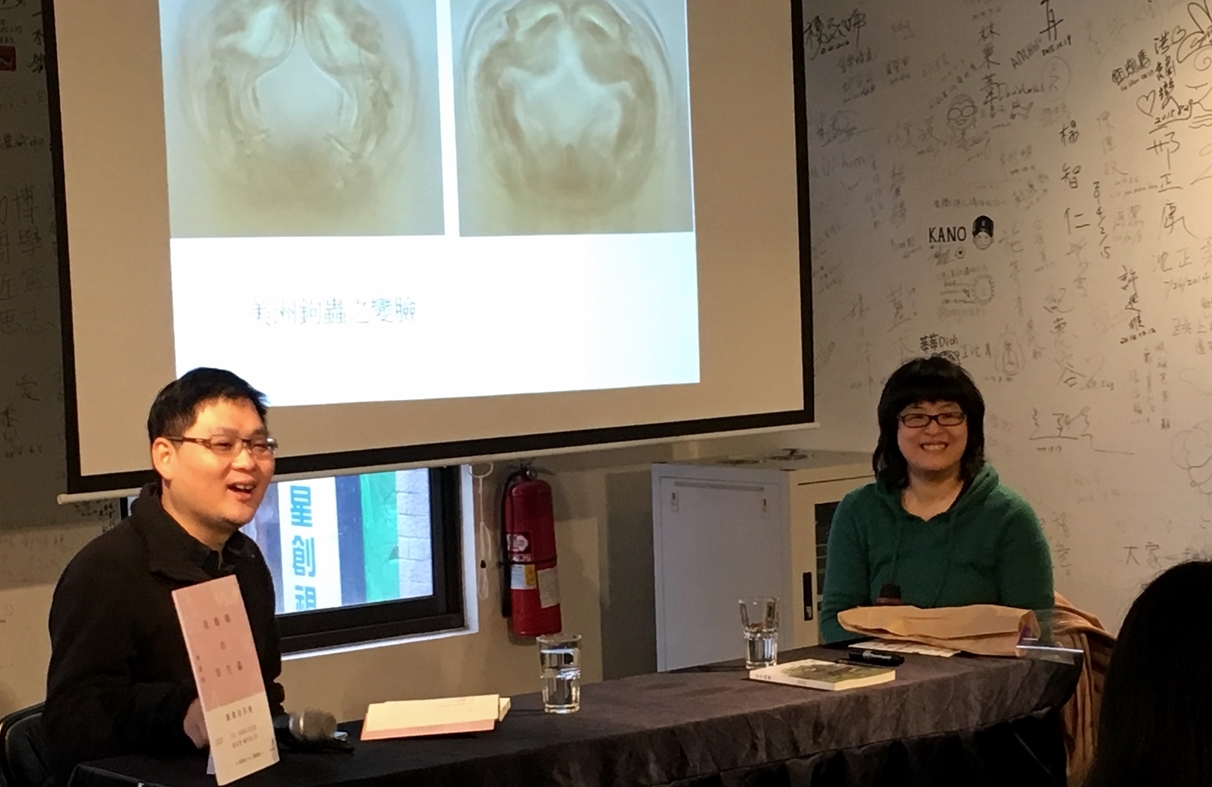
文字是最舒服的表達方式
十二歲時在仁愛圓環的獨立書店新元穠讀到了張系國的作品《棋王》,自此決定踏上作家之路。文學是最初的志向、是一生的興趣,也是最習慣的工具,文字同時具有的親密與距離感,更讓她能夠與讀者在相異的時空進入彼此的內心。欣賞超現實主義作家Unica Zürn用美麗又魔幻的文字描寫精神病房的遭遇,寫自己,也寫他人;喜歡艾利森貝克德爾的《歡樂之家》、書寫身世的柳美里、舒茲筆下的《鱷魚街》,能夠笑看家庭黑暗面的作品特別能夠引起她的共鳴。因為翻譯的長期經歷,注意到語文的傳遞特質,不只是作者用來自我抒發的東西,而是溝通的工具,希望自己能以簡單卻直接的文字直搗核心,精準銳利,絲毫不拖泥帶水。「現在有很多人會說我的文字風格平易近人,這個是我很努力去追求的東西」。如同波蘭文對她而言就像一杯純淨的伏特加,沒有任何添加,卻醇厚濃烈,又甚至僅同一杯水,乾淨澄澈。林蔚昀的文字是透明的,單純坦蕩得讓人無所遁隱,又能燒得人渾身發燙,往心頭上刻下看不見的字跡。
人在特定時空中的存在事實或許像個冰涼固體,其中所包覆的情感卻是帶有熱度的液態樣貌,隨時都可能從微小鏬隙之中流瀉而出。問起這些故事的真實性,林蔚昀說:「散文作品也能夠有虛構情節,就像我們常會說那個電影、小說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故事可能是虛構的,但你的感覺、感情是真的,我覺得創作上不必那麼去在意,某一個細節到底有沒有真的發生,也許在現實中沒有發生,但是它在某一種層面,思想或是情感的層面上有發生,那我們也可以把它當成是真的。」《大便(三)》中奶奶葬禮上的流出經血的尷尬場景,其實是外婆葬禮上真實、卻不被允許的尖銳哭泣(司儀說:「小姐,妳哭得太大聲了,可不可以哭小聲一點?」),深刻悲憤埋葬在虛構的荒謬之中。何謂真實?何謂虛構?從文學的角度來看,當中界限並不是很明確,一個個暗語,直指真實經歷的傷口,當下讀來感覺合而未癒,像用指尖挑開久未脫落的痂。
撰寫「我媽媽的寄生蟲」的過程中多次遭遇瓶頸,大多是考量讀者對母親的觀感、對先生的想法,最後才是自己可能遭受的眼光。「擔心大家會說我在無病呻吟啊…,但我很誠實地把自己的東西交代出來,那我覺得我最大的優點應該就是誠實吧。」 面前的林蔚昀是一個勇敢無比的人,時而開懷大笑,時而沉默靜思,時而語速急促地要將「她」分享給你。平實、幽默的文字裡包覆了太深的疼痛,坦白得讓人不禁開始反省自己身上是否覆蓋了過多的偽裝。二十五則家族故事,從蟲卵、幼蟲,到成蟲,她化作各式型態的蟲體,在腐敗中生長、衝突中蛻變,雖是已經完成的過去式,卻在回顧、書寫的過程中,有了再次省視傷口的機會,重新以一個女兒、一個妻子,尤其以一個母親的身份,感受自過去流動至今,尚在進行中的生命篇章。存在過的痕跡不會消失,但是因為做了選擇,緊繃的疙瘩終能鬆緩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