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孫知行「卡通頻道」
孫知行的展場入口處有一大堆箱子,從地面頂到天花板,遠看像是一座紙箱組成的島嶼,走近會發現這些箱子是投影機的素面盒子,有一些器械構造標示在表面。順著這個箱島較為低緩的部分看去,有一台小台的投影機,前方打出有如分鏡圖的卡通短片,內容說的是一個割草的人想要成為高爾夫球選手但是最後失敗。鄰近島的一面牆掛著四張圖像,圖像內容是影片中某一格的輸出,裡面有像鴕鳥的人,高爾夫球球洞與旗幟,還有投影機的介面圖。這些圖像都是用黑白電繪而成,有些地方感覺像是操作滑鼠不熟練所畫出的線條。遠離島的牆面放著一張大幅的影像,裡面有很多電器的操作指示,但是這些指示一點都不複雜,甚至沒有必要。



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作品?或許可以從創作者的創作歷程來考慮。孫知行過去的作品多像是一種社會行為的模擬,譬如做一個雜貨店。他自己説「其實都是在做行政」,不管這個行政的動作是幕前還是幕後。但是2019這一年他開始以卡通短片來創作。這些東西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嚴肅,或者說更多了一些「白爛」的趣味。但是就站在一個後設的角度去看待社會這一點上,孫知行這次的作品與之前的創作是一致的。只是他的角色從一個行動的參與者,變成了一個編劇。他一樣在觀看社會運作的邏輯,然後試圖把其中的某個部分轉化。
但是這並不能完全說明他的作品,大多數的當代藝術家也喜歡從社會之中取材,並且宣稱從事一種轉化的工作,這幾乎是當代藝術的某種範式。孫知行這次展出的作品,特殊之處是它從社會轉化至某種可以稱之為作品的過程非常「不藝術」。在這裡我們說的藝術指的是一種精準轉換的能力,譬如把社會現象抽取出一種荒誕,把商業包裝中提煉出形式,把現成影像組織成蒙太奇。孫知行沒有要做這個,從他拿起筆的一開始就是這樣。
事實上,他根本沒有拿起筆,他是用滑鼠畫出那些影像,而他宣稱原因是:「人家說手繪很自由,但是我手繪的時候卻感覺被束縛了,反而用滑鼠讓我顯得很自在。」他並沒有要透過手繪來展現某種藝術的技藝。這種反精練的傾向也展現在他對於科學(譬如重力)的引用。「大家都以為我很懂科學,其實我沒有。」這就不奇怪孫知行短片當中關於力學的描述是很荒誕的,至少絕對不是像池田亮司那樣,把科技變成了一種感官之美。還有展場當中的那堆盒子,我們都看過現成物透過重複的堆疊如何可以看起來有氣勢又抽象,創作者並沒有這樣安排,這些箱子頂多就是一個展場空間的分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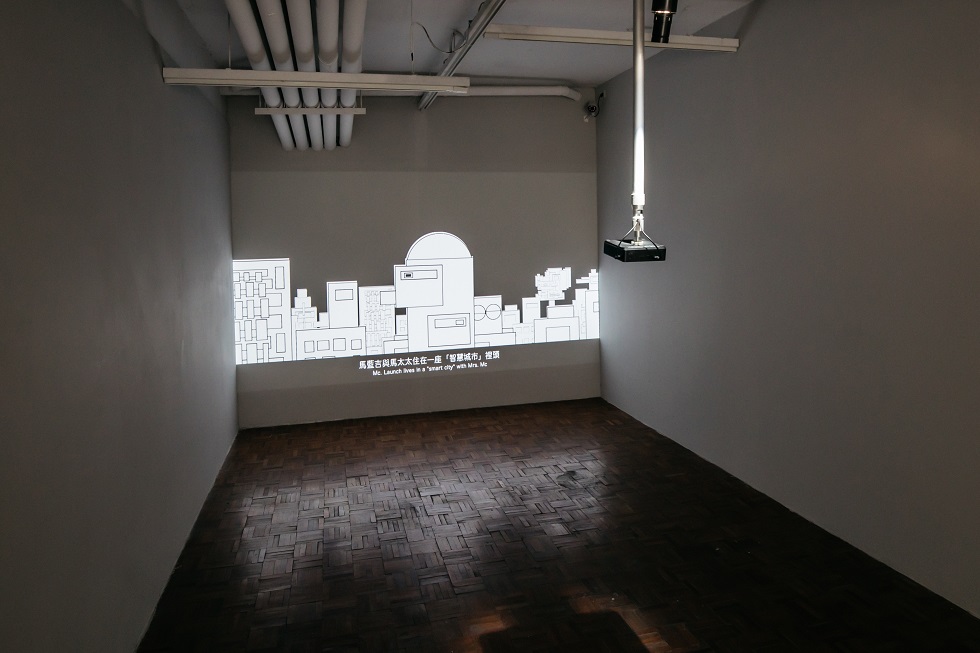
但這正是這個展覽最有趣的地方。它把關於藝術家買一台投影機的整個過程,從投影機,到說明書,到說明書的盒子,再到高爾夫球,以一種任意聯想的方式被保留下來。而創作者在其中的角色,不是一個謀劃者,而是一個且戰且走的人。創作者在說的是:我拿了一台投影機,我看看可以做出些什麼。而不是:我是一個藝術家,我要用投影機表現我的藝術。
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整組作品,就會發現其中有一個哀傷或是自嘲的氣氛。因為沒有人會像是學藝術的人這樣慎重地使用投影機,也沒有人會像創作者一樣期待投影機裡面出現了藝術,甚至於把藝術的生涯寄託在其中。而意識到這件事的人,必然是感受到某種虛幻,然而他不能用「很藝術」的方式去做出來,因為虛幻的正是藝術本身。於是他不經意地將自己假扮成一個擁有高爾夫球夢的人,或是假裝他在處理力學,但最終他觀看的是藝術,或是觀看一個在試圖創作的自己。

盧冠宏「在模糊的地方打光」
盧冠宏的作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的繪畫像是新聞畫面中很獵奇的影像。第二部分是描繪各種影子,另外一部分是實體的裝置,包括一個小型的日晷,旁邊有一個燈繞著它旋轉,以及一個像是杯子的陶板,當燈光投射在上面,後面的牆面形成了一個像是人臉又像是杯影的影像。在第一組作品裡,繪畫質地有點類似照片,人物看起來都很具象,猶如正在發生某種「事件」,不論是著火的車子,還是貌似警察的角色。但是這些繪畫中的事件也如同照片一樣,因為沒有了頭尾,所以可以被做各種解讀。第二組與第三組關於影子的作品,比較缺少這種解讀的空間。



我們要如何觀看這三種作品,盧冠宏提出了「誤讀」的概念。杯子的剪影最容易理解,許多心理測驗都使用這種圖像。新聞畫面的誤讀則來自於兩個部分。一是繪畫與相片一樣去除了時間,所以容易造成各種模糊的解釋。另一個關鍵是盧冠宏在繪畫當中加入了很多具有文化意義的形象,譬如牛仔、警察或是麥當勞,而這些形象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中,會形成不同的符號。(這或許也會使觀眾想到「圖像世代」(Picture Generation)的手法,兩者都透過刻板的角色展現文化的痕跡)影子的作品跟誤讀的關係則比較隱晦。盧冠宏說:「我在思考這些影子究竟是對象還是現象,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它就會成為不同的東西。」在此我們可以發現,所謂「不同的角度」進一步分析其實有三種層次,一種是關於事物的性質(對象或是現象),一種是關於視覺的角度,譬如環繞日晷的光。第三種是文化的脈絡。
除了誤讀之外,第二個可以觀察的軸線是繪畫作為「象徵」與作為「指示」兩種不同的意涵。在類新聞事件的作品之中,繪畫是一個象徵,而象徵需要文化脈絡的輔助才得以被解讀。但是在影子系列的作品中,影子是作為一個事物的指示(證明有某物)而存在,它無需太多文化的脈絡,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影子猶如照片一樣(一張照片無論如何都暗示了有一個真實存在的對象)。然而盧冠宏的影子與照片不同的地方是,畫家在處理影子時受到過去的訓練,而照片由於自動化的比重較高,它更像是存在的直接痕跡。盧冠宏說:「我不確定我是不是因為從小學習美術,所以對於影子就有一種特殊的觀點,這跟人們誤讀新聞畫面或許是類似的。」


第三個可以觀察的軸線是:關於繪畫的角色,盧冠宏說:「繪畫作為一個長久發展的媒材,它曾經在某一段時間,有一個派別非常著意描繪影子的存在。所以我描繪了歷史上使用影子不同的方式。」但他說的不只是影子,其實也是繪畫。繪畫作為一種真實的附隨,它同樣可以有不同的指涉,有時成為影像,有時成為對象。就狹義的理解,盧冠宏在思考繪畫如何在當代藝術之中有新的功能,他試圖告別繪畫作為一種形式技法層次的藝術,或者如他所述:「在當代藝術世界,你做為一個繪畫的人,自然就會開始思考繪畫的定位。」但是從更廣泛的意義去考慮,他問的問題是從柏拉圖的洞穴一路橫跨到了當代的新聞媒體,藝術在此既非真實之光也不是如影之幻象,而是在這兩者之間的東西。
